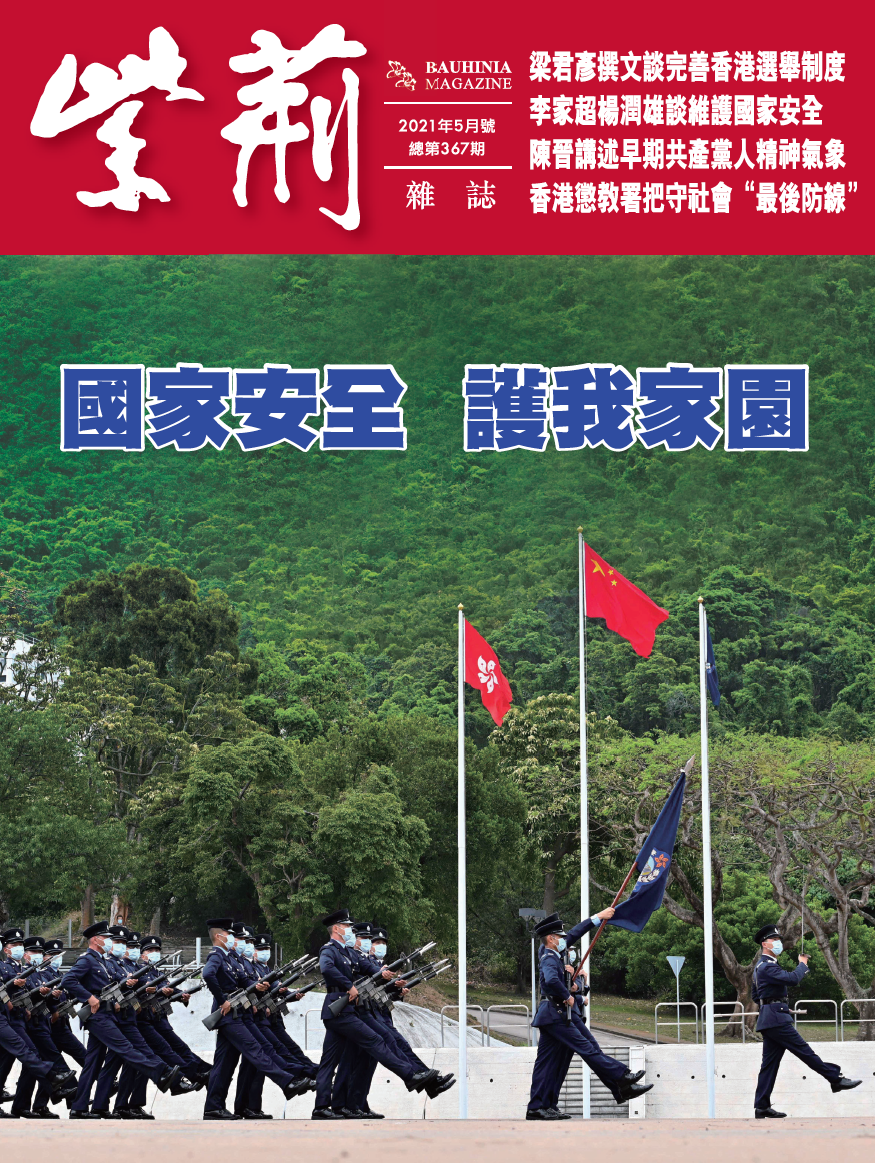編者按:值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之際,黨史學習教育中央宣講團成員、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原院務委員陳晉為本刊撰寫特稿,生動講述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鮮為人知的革命故事,幫助讀者了解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氣象,感受中國共產黨的偉大精神譜系。

充滿朝氣、樂觀積極,著眼未來、敢想敢幹,這是早期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優勢。圖為油畫《啟航——中共一大會議》(作者:何紅舟黃發祥)
2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提出,“全黨同志要做到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我的體會是,“學史明理”,就是要明白馬克思主義為什麼行、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這三個道理;“學史增信”,就是要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學史崇德”,就是要傳承和弘揚中國共產黨在100年歷史中積累起來的偉大精神和紅色基因;“學史力行”,就是要多實踐、辦實事、開新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學黨史要發揮四個方面的作用。我認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的精神氣象也蘊含了這四個方面。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有什麼樣的精神氣象,可以從以下四點進行解讀:一、100年前建黨,這不是一個人或者十幾個人、幾十個人的願望,而是先進知識分子的群體性選擇。二、早期參加建黨,包括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前入黨的那群年輕人,具備特有的組成特點和精神氣象。三、早期黨的領導層不成熟、不穩定。四、毛澤東最終脫穎而出,歷史和人民選擇了毛澤東。中共一大前,各地早期共產黨組織成員共有58位。關於到底有多少位代表參加中共一大,有12人之說,也有13人之說。新近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的表述方法是,先列出12位代表的名字,再加一句:“包惠僧受陳獨秀派遣,出席了會議”,這種敘述是很客觀的。他們代表當時全國58名黨員,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此外,不在58個人當中的一些人,也應該被視為建黨群體中的重要成員。比如蔡和森,他最早提出黨的名字叫“中國共產黨”。1920年7月,蔡和森在留法新民學會會員召開蒙達尼會議上提出,要“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同年8月,他又寫信給毛澤東,再次表達了這個主張。雖然蔡和森沒有參加中共一大,也不在58人名單之中,而且長沙早期共產黨組織也沒有他,但是在建黨成員中,他的地位與貢獻和58位黨員是不相上下的。再如惲代英。1920年夏,惲代英在湖北黃岡組建了“波社”,“波”即布爾什維克之意,其成員一致擁護無產階級專政,擁護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擁護蘇維埃,贊成組織俄國式的黨。因為沒有與陳獨秀等聯繫,所以惲代英也不在58人名單裡。“波社”成立後不久,惲代英等人獲悉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消息異常興奮,先後加入中國共產黨。還有在四川的吳玉章、楊闇公等,成立了中國青年共產黨,並給共產國際寫了報告,說明中國青年共產黨的創建情況和組織結構。因為當時四川較為閉塞,他們都不知道已經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得知有了中國共產黨,就立即把中國青年共產黨解散,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還有張太雷,雖然不是中共一大代表,但在建黨中發揮了不小作用。1920年,張太雷在北京參加了李大釗發起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為最早的黨員之一。1921年春,他受李大釗委派赴蘇聯,後任共產國際遠東局中國科科長,同年6月以中國共產黨員身份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在大會上發言談到中國國內共產黨的組建情況。其後,他多次陪同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的代表會見李大釗、陳獨秀等,並參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總體上說,當時先進知識分子群體性選擇馬克思主義、選擇社會主義、選擇共產主義,是個大趨勢,有其必然性和趨同性。中共一大之前,入黨的早期組織成員叫做建黨群體;中共一大以後到大革命失敗前,參加中國共產黨的叫做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這兩批人都可以叫做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這個群體具有三個特點,注定了黨的生命力、創造力和精神氣象。58位第一批黨員基本是知識分子,這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共性。因為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先進理念,首先在知識分子中間傳播,被知識分子接受,知識分子掌握了這個思想武器,再去動員發動工人和農民。這些知識分子具有一些共性。一是他們對信念有理論自覺和政治自覺。1921年元旦,在新民學會長沙學員新年大會上,學會成員們對選擇信仰這個問題進行熱烈討論,各抒己見。毛澤東最後總結說,擺在我們面前有五種選擇,社會政策派、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主義、列寧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經過反復比較研究,毛澤東認為,“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採用”。就在一個月前,毛澤東給在法國的新民學會會員蔡和森、蕭子升等寫了一封長信。他在信中談到,“我覺得用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採,單要採這個恐怖的方法”,意思是只能走俄國式革命的方法來改造中國這條路。可以說,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行不行、社會主義好不好、共產黨能不能幹成,進行了反復思考後才作出選擇,多數人有發自內心的信念,對初心使命有恒心、能堅持。這就體現了知識分子建黨的思想自覺和政治自覺。二是他們具有文藝氣質並能將政治信念轉化成文化自信。文化氣質對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樹立共產主義信念發揮了特殊作用,他們用多種途徑將政治信念轉化成文化自信,這是其它政黨很少有的特點。瞿秋白是把《國際歌》翻譯成中文的第一人。1935年2月,因叛徒出賣,他在福建長汀被捕。即將被執行槍決前,敵人把他押到山坡上,行至羅漢嶺一處綠地,他笑著點頭,“此地甚好!”面對敵人的子彈,他依然從容不迫,鎮靜地說: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過去忙於革命,很少大休息,今後我要大休息了。就這樣,瞿秋白高聲唱著自己翻譯的《國際歌》英勇就義。這種信念,這種境界,這種精神氣象,就是早期共產黨人的文化氣質帶來的對政治信念的自信。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詩人,越是面對逆境危急時刻,他的詩情越恣意張揚,長征途中揮筆寫下的《七律.長征》《憶秦娥.婁山關》《念奴嬌.昆侖》《清平樂.六盤山》等詩歌,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堪稱經典之作,至今仍被人們吟誦品評。陳毅也愛寫詩,在梅嶺被國民黨四十六師圍困時創作了《梅嶺三章》,其中一篇寫到:“斷頭今日意如何?創業艱難百戰多。此去泉台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豪邁的詩句表達了雖身處險境,但始終堅持獻身革命的決心和對革命必勝的信心。周恩來曾說,巴金寫了長篇小說《家》,等我退休後,我要寫一篇小說《房》,就寫周氏家族。周恩來蕩漾在內心深處的文化氣息,彌漫著共產黨人的牢固信念和深刻的理性思維。早期共產黨人是被先進文化武裝起來的,越到關鍵時刻、遇見曲折困難,他們越不會灰心喪氣。三是他們歷經磨難和經受考驗。知識分子有理論、有信仰,但需要與實踐結合,與工農結合,才能成熟。一路走來,大浪淘沙,有人堅守初心,有人落後時代。總地來說,一大批黨員經受住了重重考驗,或為共產主義事業犧牲,或看到了新中國成立,他們是黨的主流。還有一小部分人脫黨,大革命高潮時全國有5.8萬名黨員,後來只剩下1萬多人,不少是被國民黨殺害,其他的則脫黨了。不過脫黨不反黨,一些人依然堅持馬克思主義,繼續開展進步事業,包括李達、郭沫若、茅盾等。還有少數人走向反面,從“紅船”出發,但是半途當中“跳船”了,跳了以後還要拿斧頭去鑿共產黨這艘船,包括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等黨的叛徒。有人做過統計,58個第一批黨員中,只有8個人後來叛變投敵。
先進知識分子群體性選擇馬克思主義、選擇社會主義、選擇共產主義,是個大趨勢,有其必然性和趨同性。圖為2月28日,浙江省台州市仙居縣外語學校小學部,孩子們與黨旗合影(圖:中新社)
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大多出身中等人家,本有美好前途,但他們選擇馬克思主義,加入中國共產黨,不是為了謀求個人出路,而是胸懷大志,一心為了改變國家、民族、人民的命運。這種崇高的道德感帶來兩個結果:一是培養了自我犧牲精神,二是形成了同志關係紐帶。1920年,本是張太雷從天津北洋大學法科畢業的日子。但在那時,張太雷放棄了大好工作機會,從事秘密革命活動,自覺走上職業革命家的道路。1921年1月,張太雷動身前往蘇聯,此後再未有機會回津領取畢業證。他不是不珍惜這張畢業證,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事業上了。這張畢業證至今仍存放在天津大學檔案館,作為“鎮館之寶”。彭湃是大家庭出身。當時有種說法,烏鴉都飛不過彭家的田產,足見彭家家業之豐厚。但接受了先進思想的彭湃,當著佃戶的面把田契燒了。這把火燒掉了至少70石租的田產,一瞬間彭湃從富家子弟變成了“無產者”,從地主大少爺變成了“農民運動大王”。毛澤東年輕時,有一次到同學家作客,那位同學當著他的面把僕人叫來交待去買肉的事,引起毛澤東的反感,認為這個同學過於低俗,從此不再交往。毛澤東後來回憶起這件事還申明說,“我的朋友和我只願意談論大事——人的天性,人類社會,中國,世界,宇宙!”什麼叫同志關係?可以從一塊手錶說起。1920年,瞿秋白以記者身份到蘇聯採訪並寫下了兩本書——《餓鄉紀程》與《赤都心史》。在此期間,他看到這個國家物質緊張、經濟蕭條,於是把手上的金錶捐獻給了蘇聯政府。但採訪不能沒有手錶,蘇聯政府又回贈了他一塊鋼製懷錶。瞿秋白就戴著這塊懷錶工作。1931年,茅盾的弟弟沈澤民從蘇聯回來,當選為中央委員,黨中央派他到鄂豫皖任省委書記。臨走之時,瞿秋白、楊之華夫婦去看望他,把這塊懷錶送給沈澤民,理由是你到蘇區可能要指揮打仗,需要懷錶。沈澤民戴著懷錶到了鄂豫皖,指揮紅二十五軍打了幾仗。其中一仗與師長徐海東等人發生矛盾,意見不一致,結果證明沈澤民錯了,打了敗仗。後來沈澤民主動找到徐海東承認錯誤,臨走的時候,他一看徐海東手錶沒有了,就問你的手錶呢?徐海東說不小心摔壞了。沈澤民說我身體不好,要在後方休養一段時間,你在前方打仗不能沒有手錶,就把懷錶送給了徐海東。徐海東戴著這塊懷錶參與了鄂豫皖戰鬥、長征和抗戰。1939年,徐海東在八路軍一一五師當旅長,中央派他到蘇北新四軍任江北指揮部副總指揮兼第四支隊司令員。臨走的時候,他去見彭德懷,把這塊懷錶送給彭德懷當做紀念。還說,懷錶是沈澤民送給我的,沈澤民說是瞿秋白送給他的。而當時瞿秋白、沈澤民已經犧牲或病逝了。彭德懷戴著這塊懷錶指揮了百團大戰等重要戰役。1946年,經歷四年牢獄之災的瞿秋白之妻楊之華從新疆被釋放回到延安,彭德懷聽說後,想到這個懷錶最早的主人是瞿秋白,就找到楊之華,把這個懷錶完璧歸趙。雖然懷錶最終物歸原主,但最早的主人瞿秋白已經犧牲了。現在這塊懷錶收藏於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這就是同志關係。哪怕同志之間在工作中有爭論,但感情牢固且純粹,表達感情的方式就是把自己最珍貴和最需要的東西交付給對方。100年前建黨的那批人,用現在的話說,除了極個別屬於當時的“80後”,基本上都是“90後”,還有少數“00後”,主體是“95後”。中共一大代表中就有19歲的年輕人。所以說,中國共產黨是個年輕的政黨。那些年輕人對早期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塑造幾乎很難被複製,因為他們都接受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從年齡結構來看,大革命失敗前,除了陳獨秀年長些之外,在中央機關工作的,大都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所以當時陳獨秀在黨內的外號叫“老頭子”。大革命失敗後,中央領導層仍然以年輕人為主。瞿秋白、李立三先後主持工作,當過一把手,那時瞿秋白28歲,李立三29歲。王明27歲成為中央領導人,博古24歲時成為黨的總負責人。任弼時23歲進入中央政治局,24歲入選中央政治局常委,是黨史上最年輕的政治局委員。鄧小平25歲到廣西領導起義,陳雲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時29歲。在根據地指揮打仗的紅軍的軍長、師長,大多是20多歲的年輕人。這是一個年輕人組建的政黨,充滿朝氣、樂觀積極,著眼未來、敢想敢幹,這是早期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優勢。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確實是幹大事的。如今,歷經百年的中國共產黨從理論到制度,各方面都已經非常成熟,我們要格外珍惜。但早期中國共產黨的中央領導層尚不成熟,領導層變動很頻繁,一個不行了,就換另一個上來。鄧小平後來講,“在歷史上,遵義會議以前,我們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不成熟、沒有能力,這是鄧小平對早期中央領導層的評價。為什麼這麼說?因為當時時局惡劣,敵強我弱,領導層恰恰是在危機中出現。在危機中方能檢驗一個領導層有沒有能力、成不成熟,這是很重要的。一群年輕人領導一個年輕的政黨,帶有不成熟的特點在所難免。原因在於:黨在組織上不獨立,屬於共產國際領導,選擇中央領導人時,經常要由共產國際來主導安排;黨在理論上不成熟,犯了教條主義錯誤,沒有能夠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建立起能夠武裝頭腦的理論;再就是能力上不適應。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經歷了兩次高潮、兩次低潮,直到確立毛澤東同志在黨內的領導地位,才結束了這種不成熟的狀態。
中國歷史最終選擇了毛澤東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集中全力解決軍事和組織問題。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圖為遵義會議會議室原址(圖:中新社)
比較一下毛澤東之前黨的五位一把手,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張聞天,他們的理論水平、政策水平都很高,但是不擅長軍事領導,缺乏指揮軍隊打勝仗的能力。革命年代,黨要生存,不僅需要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更需要軍事統帥。軍事統帥如果不在中央領導層,是有問題的。為什麼歷史最終選擇了毛澤東?首先他是軍事領袖。毛澤東在1935年遵義會議復出,因為黨在軍事上需要他。從遵義會議到陝北初期,毛澤東展現了傑出的軍事能力和才華,黨內有同志稱呼毛澤東為“毛大帥”。此後,在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從蘇聯回來的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國共產黨要以毛澤東為首來解決問題,共產國際支持毛澤東的中共領袖地位。這樣毛澤東從軍事領袖成為政治領袖。再後來,通過延安整風等運動,毛澤東又成為理論領袖。從軍事、政治到理論,毛澤東完成了被歷史選擇為領袖的過程。在這當中,理論成熟很重要,理論上的成熟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壯大和中國共產黨走出早期的不成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毛澤東在軍事上寫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在哲學上寫了《矛盾論》《實踐論》等,在政治上寫了《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人〉發刊詞》等,在文化上寫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在經濟上寫了《陝甘寧邊區的財政經濟問題》等。這一系列切合中國實際的論著,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地、系統地呈現出來。全黨接受了思想上的洗禮,為中國共產黨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礎。吳玉章曾說,《論持久戰》的發表,使毛澤東贏得了全黨同志發自內心的、五體投地的讚許、佩服甚至崇拜,從而最終確立了在黨內無可替代的領袖地位和崇高威望。所以,《論持久戰》的發表,毛澤東以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嫻熟應用和對抗日戰爭的透徹分析,征服了全黨同志,全黨感到經過十多年的曲折歷史終於鍛煉並篩選出自己的領袖,這種從感情上對毛澤東領袖地位的認同與擁戴,與一般的組織安排絕不可同日而語。
編輯:嚴 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