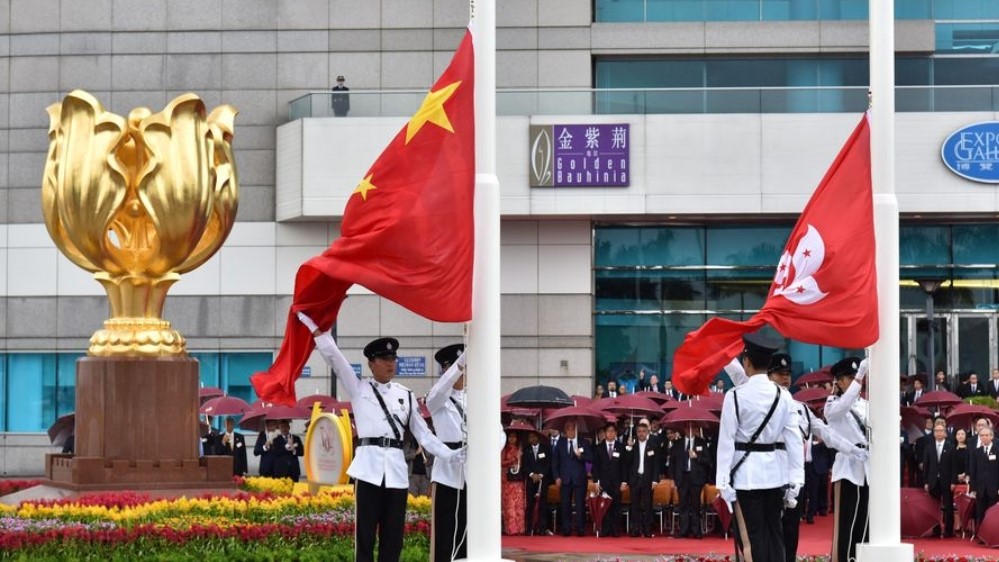
《香港國安法》確實起到了對香港民主習慣進行「移風易俗」的規範性作用。
今年6月,香港民主派焦躁不安,異常不適:維園集會未獲批准,參與者有嚴重的法律風險;「七一」大遊行前景不妙,估計也會泡湯。香港的「民主節日」似乎都過不了了,香港的民主傳統還能存續嗎?這不僅僅是所謂普選前景問題,更是日常習慣的民主生活方式問題。「一國一制」、「香港民主已死」、「舊有的香港自由已逝」之類的悲情哀嘆之聲,在香港本地和國際輿論場時有爆發,刺激港人敏感神經。如何理解香港民主習慣之變呢?如何理解國家對「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垂直立法帶來的深遠影響呢?「一國兩制」與香港民主的前景會是怎樣的?這些疑問是深刻而複雜的,也會是持久的,甚至是冒犯性的,不會因為中央的立法說明與宣傳,以及特區政府的本地立法完成,而煙消雲散。新制度與香港人心的內在溝通,才剛剛開始。
香港的民主習慣是獨特的,是殖民遺產與「一國兩制」碰撞糅合的產物。2014年訪學港大期間,筆者不僅有機會全程現場觀摩「佔中運動」,而且對「六四」維園集會與「七一」大遊行印象深刻,更對立法會內的「花式拉布」與校園民主的「天真爛漫」頗為感觸,對外部勢力控制香港民主的程度感到驚駭。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民主保持着高亢的精神氣質,並以「民主回歸論」的香港普選目標,甚至「民主中國」的遠端目標作為共識基礎。為了「民主」這樣的普適價值,香港的民主派不惜與具體的國家及其背後的領導性力量——中國共產黨為敵。香港民主在形式上可能是吸引人的,也有對西方民主的技術模仿,活躍於民主運動角落的每一個人,也許確實分享着民主的普適榮光,但喪失國家前提的民主自滿和民主激進化,卻為這一絢爛的現代政治進程蒙上了濃重的陰影。民主背離愛國的前提,是香港政治衝突不斷激烈化的思想根源。
今年的維園集會再次告吹,警方沒有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意味着強行集會有違法風險,不僅涉嫌「非法集結」,而且涉嫌違反國安法。未獲批准,法律理由上當然可以歸向疫情防控,但更本質的理由自然是國安法。不僅傳統集會難以合法進行,甚至組織集會的「香港支聯會」本身的合法性,尤其是「顛覆綱領」(結束一黨專政)涉嫌觸犯國安法的問題,也再次浮現出來。支聯會方面堅稱不會修改任何綱領,而且表示他們的「民主綱領」一貫如此。一貫如此就合法嗎?是否合法需要根據具體法律規範判斷,在國安法條件下,原來的法律灰色地帶已經不存在,規範清晰化必然帶來原有民主習慣的「移風易俗」。如果維園集會的習慣改了,預期「七一」大遊行的習慣也會改變,「民陣」的法律命運與「支聯會」類似。
如果追溯歷史,維園集會及其支聯會組織方是1989風波之運動遺產的轉移存續。儘管這一傳統並不主張「港獨」,但對國家制度和政權具有「顛覆性」,是一種政治革命的訴求,有着「顏色革命」的底蘊。《香港國安法》專門規定了「顛覆國家政權罪」,可覆蓋此類組織及其行為。「七一」大遊行則是2003年反對23條立法的結果,後來逐漸成為「民主抗中」的政治大雜燴,有「港式民主節日」的意蘊。許多港人或許以此為榮,認為這些民主習慣不僅是香港自己創造和維繫的,也對「民主中國」有重要推動作用。然而,它們或者延續顛覆性政治革命訴求,或者直接反對香港國安立法(23條),後續發展中更是與外部勢力及本土極端勢力存在勾結與合流,其合法性缺陷早就存在,只是一直缺乏清晰的法律規範與執法意志加以衡量和糾正。
為什麼這些民主習慣「一貫如此」,而如今卻必須「改弦更張」呢?最直接的理由當然是《香港國安法》,在清晰的法律規範下,執法機關必須嚴正執法,民主行動者必須遵守新法,調整適應。因為就「一國兩制」的法秩序利益而言,國家安全是前提性和基礎性的,反對這一前提和基礎的民主習慣必須改變。但這並不意味香港民主習慣及其自由權利的真正喪失,而是需要自我調適到合法的範疇之內,比如支聯會明確刪除「顛覆綱領」,並切斷與外部勢力的勾結,以及「民陣」等組織在活動申請中與本土極端派及外部勢力明確劃清界限,並嚴格遵守國安法。這樣的「法律適應化」改造,對習慣了自由自在、風光無限的香港民主派而言,是非常苦澀和艱難的。
香港許多民主派無法適應新制度,這是客觀存在的。他們被標籤為「反中亂港」勢力而決定性出局,儘管基本成為事實,但內心並不服氣,所以有不同的政治選擇:
「跑路派」走「港獨」國際路線,因為進入國際空間後更加肆無忌憚,當然也會逐步過氣和邊緣化;
「退出江湖派」即退出政壇、金盆洗手,對新制度不主動適應,也不刻意反對,這些人通常是民主元老(老江湖)或者專業精英(有專業收入保障);
「壓力團體派」,即重走體制外的壓力活動路線,但因國安法的存在,其活動形式與強度均受到限制。
這就導致了香港「一代人」的民主青春之「芳華已逝」,民主精英出現結構性流失,即便有些溫和反對派成功改造為「忠誠反對派」,其底氣與元氣也難以恢復。民主的活力其實不在制度,而在人心,在精英的責任倫理和大眾的團結基礎,如果精英萎頓,大眾分裂,民主就會成為衝突對抗的亂源。因此,香港民主要想獲得生機與活力,除了中央承諾的「不是清一色」之外,還需要香港精英的負責任轉型和大眾的理解適應。隨着香港選舉制度本地立法的完成,新制度在規範建構上已經結束,新的民主遊戲規則和制度軟體系統已經裝載完畢,下面就是功能測試和檢驗的週期了。
新選制要防止被本土派和外部勢力破壞,防止出現「選舉不合作運動」或「選舉攬炒主義」對香港民主的進一步傷害。因此,新選制的「首秀」就需要大量紮實的制度宣傳與組織動員工作,特別是支援和鼓勵非建制派的「忠誠轉化」,確保新選制的民主包容性和社會認受性,確保「愛國者」的社會光譜覆蓋面。當然,入局者需要資格審查,是有嚴格條件和標準的,香港民主選舉不能重演過去的衝突遊戲,但資格審查在「首秀」階段也不宜把關過嚴而挫傷香港社會的民主信心與積極性。新選制的開放度和非建制派的參與度,是香港民主新秩序的核心指標。我在即將出版的新書《香港新秩序:國安與民主的雙重變奏》中,更加系統完整地討論了香港民主新秩序的轉型發展問題。此時頭緒和糾結頗多,理論闡明和制度解釋不易,疏解人心與引導行動更不易。但「一國兩制」從來都是實驗性、挑戰性、創新性與整合性並存的活力體系,眼下的艱難困頓正是新制度創生的前夜風景。
本來香港的政治自由充沛,中央權力高度節制,民主發展道路開闊,為何一步步演化至此呢?香港民主的體質與基因是特殊而多元的,其高亢入場和慘烈轉型有著如下基本因素:
港英殖民統治留下的制度遺產和政治人才,尤其是1980年以來的「急速民主化」帶來的民主立場與行為習慣,和「一國兩制」尤其是「愛國者治港」之間存在規範性對抗,香港民主在基因上沾染殖民印記和反中衝動;
愛國愛港力量長期遭受政治壓抑,人才鍛煉與成長受到抑制,在實際政治能力和社會認受性上存在短板;
香港的歷史人口存在與大陸主體歷史的「反對」關係,是受排斥者的歷史集合,他們的家族史和個人史助長了「民主抗中」共識的形成及其實踐化;
中央過於節制的權力行使習慣及特區政府管治政策的失當,導致國家權威與特區政府權威始終難以有效建立,在2019年修例風波中,這種權威缺失的程度近乎「無政府」狀態,倒逼中央改變了原來的「道家式治港」,而立足國家利益與國家理性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法家式治港」的決斷意志和制度嚴厲性;
「民主回歸論」本身存在僵化和機會主義缺陷,既無法真誠轉型為「忠誠反對派」,又無法抵禦本土主義挾持和誘惑,導致香港民主運動日益脫軌,走向「一國兩制」的對立面;
英美勢力對香港民主的組織體系與行動路線有着長期而深刻的塑造、控制和煽動,導致香港民主「棋子化」,缺乏立足「一國兩制」的穩健政治立場和國家觀念認同,在中美新冷戰的波動期終作為「棋子」,而釋放出了全部的政治對抗能量,修例風波正是其能量極值,也是香港民主運動由盛轉衰的拐點。
總之,在國安法理由及其執法壓力下,「二次佔中」、「二次反修例」都已成民主運動的歷史絕響,常規性的維園集會和「七一」大遊行,就其合法性及影響力而言正面臨崩解,香港民主的自我傳統與習慣確實在改變。面對這一劇變,香港社會需要一場有關「一國兩制」與民主的再啟蒙和再教育,要敢於反思檢討過往錯失,尋回地方民主的國家前提,告別對本土勢力和外部勢力的依賴習慣,真正立足憲法與基本法構成的特區憲制秩序展開民主重建。
在此意義上,《香港國安法》確實起到了對香港民主習慣進行「移風易俗」的規範性作用,甚至這一部法律具有「一國兩制」之「去殖民化+去本土化」綱領的地位,其深遠的民主法治重塑意義,會因時間拉長和距離變遠而更加凸顯。民主歸去,民主會再來,因為「一國兩制」還在,因為國家支持香港民主有序發展的決斷意志和憲法基礎並未改變。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來源:橙新聞
掃描二維碼分享到手機
![]()
+關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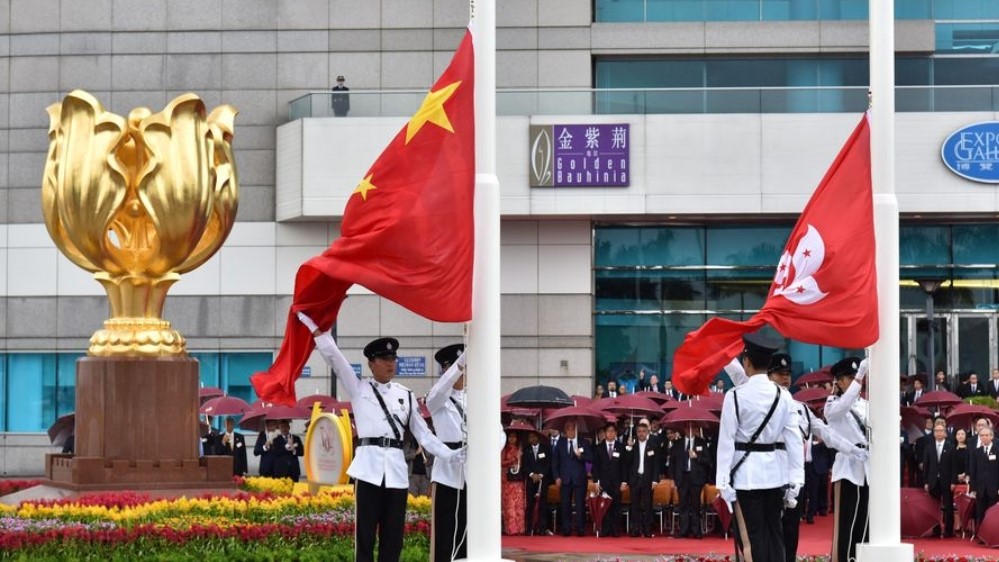
《香港國安法》確實起到了對香港民主習慣進行「移風易俗」的規範性作用。
今年6月,香港民主派焦躁不安,異常不適:維園集會未獲批准,參與者有嚴重的法律風險;「七一」大遊行前景不妙,估計也會泡湯。香港的「民主節日」似乎都過不了了,香港的民主傳統還能存續嗎?這不僅僅是所謂普選前景問題,更是日常習慣的民主生活方式問題。「一國一制」、「香港民主已死」、「舊有的香港自由已逝」之類的悲情哀嘆之聲,在香港本地和國際輿論場時有爆發,刺激港人敏感神經。如何理解香港民主習慣之變呢?如何理解國家對「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垂直立法帶來的深遠影響呢?「一國兩制」與香港民主的前景會是怎樣的?這些疑問是深刻而複雜的,也會是持久的,甚至是冒犯性的,不會因為中央的立法說明與宣傳,以及特區政府的本地立法完成,而煙消雲散。新制度與香港人心的內在溝通,才剛剛開始。
香港的民主習慣是獨特的,是殖民遺產與「一國兩制」碰撞糅合的產物。2014年訪學港大期間,筆者不僅有機會全程現場觀摩「佔中運動」,而且對「六四」維園集會與「七一」大遊行印象深刻,更對立法會內的「花式拉布」與校園民主的「天真爛漫」頗為感觸,對外部勢力控制香港民主的程度感到驚駭。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民主保持着高亢的精神氣質,並以「民主回歸論」的香港普選目標,甚至「民主中國」的遠端目標作為共識基礎。為了「民主」這樣的普適價值,香港的民主派不惜與具體的國家及其背後的領導性力量——中國共產黨為敵。香港民主在形式上可能是吸引人的,也有對西方民主的技術模仿,活躍於民主運動角落的每一個人,也許確實分享着民主的普適榮光,但喪失國家前提的民主自滿和民主激進化,卻為這一絢爛的現代政治進程蒙上了濃重的陰影。民主背離愛國的前提,是香港政治衝突不斷激烈化的思想根源。
今年的維園集會再次告吹,警方沒有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意味着強行集會有違法風險,不僅涉嫌「非法集結」,而且涉嫌違反國安法。未獲批准,法律理由上當然可以歸向疫情防控,但更本質的理由自然是國安法。不僅傳統集會難以合法進行,甚至組織集會的「香港支聯會」本身的合法性,尤其是「顛覆綱領」(結束一黨專政)涉嫌觸犯國安法的問題,也再次浮現出來。支聯會方面堅稱不會修改任何綱領,而且表示他們的「民主綱領」一貫如此。一貫如此就合法嗎?是否合法需要根據具體法律規範判斷,在國安法條件下,原來的法律灰色地帶已經不存在,規範清晰化必然帶來原有民主習慣的「移風易俗」。如果維園集會的習慣改了,預期「七一」大遊行的習慣也會改變,「民陣」的法律命運與「支聯會」類似。
如果追溯歷史,維園集會及其支聯會組織方是1989風波之運動遺產的轉移存續。儘管這一傳統並不主張「港獨」,但對國家制度和政權具有「顛覆性」,是一種政治革命的訴求,有着「顏色革命」的底蘊。《香港國安法》專門規定了「顛覆國家政權罪」,可覆蓋此類組織及其行為。「七一」大遊行則是2003年反對23條立法的結果,後來逐漸成為「民主抗中」的政治大雜燴,有「港式民主節日」的意蘊。許多港人或許以此為榮,認為這些民主習慣不僅是香港自己創造和維繫的,也對「民主中國」有重要推動作用。然而,它們或者延續顛覆性政治革命訴求,或者直接反對香港國安立法(23條),後續發展中更是與外部勢力及本土極端勢力存在勾結與合流,其合法性缺陷早就存在,只是一直缺乏清晰的法律規範與執法意志加以衡量和糾正。
為什麼這些民主習慣「一貫如此」,而如今卻必須「改弦更張」呢?最直接的理由當然是《香港國安法》,在清晰的法律規範下,執法機關必須嚴正執法,民主行動者必須遵守新法,調整適應。因為就「一國兩制」的法秩序利益而言,國家安全是前提性和基礎性的,反對這一前提和基礎的民主習慣必須改變。但這並不意味香港民主習慣及其自由權利的真正喪失,而是需要自我調適到合法的範疇之內,比如支聯會明確刪除「顛覆綱領」,並切斷與外部勢力的勾結,以及「民陣」等組織在活動申請中與本土極端派及外部勢力明確劃清界限,並嚴格遵守國安法。這樣的「法律適應化」改造,對習慣了自由自在、風光無限的香港民主派而言,是非常苦澀和艱難的。
香港許多民主派無法適應新制度,這是客觀存在的。他們被標籤為「反中亂港」勢力而決定性出局,儘管基本成為事實,但內心並不服氣,所以有不同的政治選擇:
「跑路派」走「港獨」國際路線,因為進入國際空間後更加肆無忌憚,當然也會逐步過氣和邊緣化;
「退出江湖派」即退出政壇、金盆洗手,對新制度不主動適應,也不刻意反對,這些人通常是民主元老(老江湖)或者專業精英(有專業收入保障);
「壓力團體派」,即重走體制外的壓力活動路線,但因國安法的存在,其活動形式與強度均受到限制。
這就導致了香港「一代人」的民主青春之「芳華已逝」,民主精英出現結構性流失,即便有些溫和反對派成功改造為「忠誠反對派」,其底氣與元氣也難以恢復。民主的活力其實不在制度,而在人心,在精英的責任倫理和大眾的團結基礎,如果精英萎頓,大眾分裂,民主就會成為衝突對抗的亂源。因此,香港民主要想獲得生機與活力,除了中央承諾的「不是清一色」之外,還需要香港精英的負責任轉型和大眾的理解適應。隨着香港選舉制度本地立法的完成,新制度在規範建構上已經結束,新的民主遊戲規則和制度軟體系統已經裝載完畢,下面就是功能測試和檢驗的週期了。
新選制要防止被本土派和外部勢力破壞,防止出現「選舉不合作運動」或「選舉攬炒主義」對香港民主的進一步傷害。因此,新選制的「首秀」就需要大量紮實的制度宣傳與組織動員工作,特別是支援和鼓勵非建制派的「忠誠轉化」,確保新選制的民主包容性和社會認受性,確保「愛國者」的社會光譜覆蓋面。當然,入局者需要資格審查,是有嚴格條件和標準的,香港民主選舉不能重演過去的衝突遊戲,但資格審查在「首秀」階段也不宜把關過嚴而挫傷香港社會的民主信心與積極性。新選制的開放度和非建制派的參與度,是香港民主新秩序的核心指標。我在即將出版的新書《香港新秩序:國安與民主的雙重變奏》中,更加系統完整地討論了香港民主新秩序的轉型發展問題。此時頭緒和糾結頗多,理論闡明和制度解釋不易,疏解人心與引導行動更不易。但「一國兩制」從來都是實驗性、挑戰性、創新性與整合性並存的活力體系,眼下的艱難困頓正是新制度創生的前夜風景。
本來香港的政治自由充沛,中央權力高度節制,民主發展道路開闊,為何一步步演化至此呢?香港民主的體質與基因是特殊而多元的,其高亢入場和慘烈轉型有著如下基本因素:
港英殖民統治留下的制度遺產和政治人才,尤其是1980年以來的「急速民主化」帶來的民主立場與行為習慣,和「一國兩制」尤其是「愛國者治港」之間存在規範性對抗,香港民主在基因上沾染殖民印記和反中衝動;
愛國愛港力量長期遭受政治壓抑,人才鍛煉與成長受到抑制,在實際政治能力和社會認受性上存在短板;
香港的歷史人口存在與大陸主體歷史的「反對」關係,是受排斥者的歷史集合,他們的家族史和個人史助長了「民主抗中」共識的形成及其實踐化;
中央過於節制的權力行使習慣及特區政府管治政策的失當,導致國家權威與特區政府權威始終難以有效建立,在2019年修例風波中,這種權威缺失的程度近乎「無政府」狀態,倒逼中央改變了原來的「道家式治港」,而立足國家利益與國家理性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法家式治港」的決斷意志和制度嚴厲性;
「民主回歸論」本身存在僵化和機會主義缺陷,既無法真誠轉型為「忠誠反對派」,又無法抵禦本土主義挾持和誘惑,導致香港民主運動日益脫軌,走向「一國兩制」的對立面;
英美勢力對香港民主的組織體系與行動路線有着長期而深刻的塑造、控制和煽動,導致香港民主「棋子化」,缺乏立足「一國兩制」的穩健政治立場和國家觀念認同,在中美新冷戰的波動期終作為「棋子」,而釋放出了全部的政治對抗能量,修例風波正是其能量極值,也是香港民主運動由盛轉衰的拐點。
總之,在國安法理由及其執法壓力下,「二次佔中」、「二次反修例」都已成民主運動的歷史絕響,常規性的維園集會和「七一」大遊行,就其合法性及影響力而言正面臨崩解,香港民主的自我傳統與習慣確實在改變。面對這一劇變,香港社會需要一場有關「一國兩制」與民主的再啟蒙和再教育,要敢於反思檢討過往錯失,尋回地方民主的國家前提,告別對本土勢力和外部勢力的依賴習慣,真正立足憲法與基本法構成的特區憲制秩序展開民主重建。
在此意義上,《香港國安法》確實起到了對香港民主習慣進行「移風易俗」的規範性作用,甚至這一部法律具有「一國兩制」之「去殖民化+去本土化」綱領的地位,其深遠的民主法治重塑意義,會因時間拉長和距離變遠而更加凸顯。民主歸去,民主會再來,因為「一國兩制」還在,因為國家支持香港民主有序發展的決斷意志和憲法基礎並未改變。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來源:橙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