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安法與香港法律制度:對照、分析與思考(下)
《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朱國斌I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法學博士
(二)超然於司法覆核的國安委
香港國安法既是實體法,又是程序法,還是組織法,後者主要體現在它規定了香港特區設立國安委、警務處國家安全部門等本地機構。這也是自回歸以後,中央首次直接為特區政府創制、改變特區政府內部架構。香港國安法將國安委定位為「負責特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責任」(第12條)。國安委的具體職責為:「(一)分析研判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形勢,規劃有關工作,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政策;(二)推進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建設;(三)協調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重點工作和重大行動。」(第14條)從國安委的法律定位、職權性質與組織人事來分析,它是特區政府下的一個本地機構(或至少是行政權之下的本地機構)。然而,國安法確實賦予了它超出一般本地行政機構的特權,甚至包括超然於司法覆核的特權,此即第4條第2款所指:「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不受香港特別行政區任何其他機構、組織和個人的干涉,工作信息不予公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作出的决定不受司法覆核」。
英式傳統的司法覆核,或稱行政法意義上的司法覆核(judicial review in administrative law),是香港自英國繼承而來的傳統的普通法制度。香港法院對政府部門、法定機構行使公權力的行為具有廣泛的司法覆核管轄權,並受到基本法的確認與保障:第19條規定,法院除繼續保持香港原有法律制度和原則對法院審判權所作的限制外,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所有的案件均有審判權;第35條規定,香港居民有權對行政部門和行政人員的行為向法院提起訴訟。國安委作為一個設在本地的行政機構,其所作决定不受司法覆核,是否侵蝕了法院依據基本法享有的固有的司法審查權,造成了一處「法外之地」?這是細緻的觀察者都會提出的一個問題(question)。
自回歸以來,特區法院特別是終審法院發展了司法覆核制度,使之形成為憲法意義上的司法覆核(constitutional review,judicial review of constitutional law)。里程碑式的案例就是1999年終審法院裁决的「吳嘉玲案」(Ng Ka-ling)。首席大法官李國能先生在判例中寫道:「香港特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基本法第 19(1)條),而特區各級法院是特區的司法機關,行使特區的審判權(基本法第 80 條)。在行使基本法所賦予的司法權時,特區的法院有責任執行及解釋基本法。毫無疑問,香港法院有權審核特區立法機關所制定的法例或行政機關之行為是否符合基本法,倘若發現有抵觸基本法的情况出現,則法院有權裁定有關法例或行為無效。法院行使這方面的司法管轄權乃責無旁貸,沒有酌情餘地。因此,若確實有抵觸之情况,則法院最低限度必須就該抵觸部份,裁定某法例或某行政行為無效。雖然這點未受質疑,但我等應藉此機會毫不含糊地予以闡明。行使這方面的司法管轄權時,法院是按基本法執行憲法上的職務,以憲法制衡政府的行政及立法機構,確保它們依基本法行事。」新的司法覆核制度形式上可與美式違憲審查制度類比。
然而,基於基本法,我們注意到,香港法院的司法審查權並非沒有邊界,或者應當說,法院的司法管轄權在基本法層面存在一些固有限制:(1)香港原有法律制度和原則對法院審判權所作的限制;(2)對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無管轄權的限制。鑒於職能的特殊性質,國安委行使的職權會否本身就處於基本法劃定的法院管轄權之外?香港立法中也規定有司法覆核的豁免條款,例如,《房屋條例》第19條(3)規定,「如任何人的租契已根據第(1)款終止,則法院沒有司法管轄權聆訊由該人或代該人提出的與該項終止有關的寬免申請」。對此,法院裁定仍維護了自己的司法覆核權。只是法院的這種立場很難在國安委豁免覆核的問題上得到延續,固有的司法權威受到來自中央國安立法的挑戰。
或者可以換個角度來看,國安委的司法覆核豁免,可以視作中央對特區行政「全面管治權」和主導特區政治體制的重申與强化。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國安委之間有兩個連接點:第一,國安委「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監督和問責」(第12條);第二,由中央人民政府向國安委指派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履行職責相關事務提供意見」(第15條)。鑒於中央人民政府與國安委的權力關係,國家安全顧問角色將會十分關鍵,所提供的意見可以合理想像地認為是代表中央意旨的指導性的、方向性的意見。這也客觀上反映了一種新的權力架構與職責分配:特區國家安全事務從宏觀政策層面觀之是中央事權,從行動層面觀之則是中央與特區共享事權,但主要是特區事權,特區其他國家安全機構的設立就是服務於這一目的。以此為據,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麽國安委决定不受司法覆核。但不論如何,都需理論上回應國安委權力與特區法院的司法管轄權之間的緊張關係問題,更期待司法實踐中探索厘定新的行為與互動模式。
(三)不受特區管轄的國安公署
香港國安法規定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特區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國安公署」)「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職責,行使相關權力」(第48條)。法律並規定了國安公署的四項職責(職權):「(一)分析研判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形勢,就維護國家安全重大戰略和重要政策提出意見和建議;(二)監督、指導、協調、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三)收集分析國家安全情報信息;(四)依法辦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第49條)作為中央政府駐港機構(之一),國安公署在香港特區行使職權,直接關涉到香港居民的權利與義務。按照基本法的規定與普通法的原則,行政權力的運行應當受到司法覆核的監督。但香港國安法規定國安公署及其人員「依據本法執行職務的行為,不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管轄」(第60條第1款),這意味著國安公署及其人員的職務行為至少在特區層面具有不可訴性(no judicial review of acts of the Commissioner)。這種豁免的法理基礎與合法性有待我們深入探究。
在國安公署全部的「執行職務的行為」中,香港國安法第55條關於國安公署有權直接管轄的三類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規定尤為值得關注。如上小節所述,根據法律安排,從行動層面觀之,香港國家安全事權是中央與特區共享事權。國安公署直接管轄三類法定類型案件是中央事權的體現。將其排除在特區法院管轄之外,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職務行為不受特區管轄,一方面給予國安公署更多的自主性和行動空間、更少的限制,便於其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能,另一方面,也構成對香港法治的特例,更關涉到香港國安法自身規定如何落實的問題。該法明確規定國安公署「應當嚴格依法履行職責,依法接受監督,不得侵害任何個人和組織的合法權益」(第50條第1款);國安「公署人員除須遵守全國性法律外,還應當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第50條第2款)。在此可以提出的問題是:如何保證、監督國安公署及其人員履職行為或其他行為的合法性?國安公署須遵守的全國性法律(應指在內地實行的全部法律)與香港特區的法律不一致的,應以何者為準?排除特區對國安公署及其人員的職務行為的管轄權以後,將由內地哪一主體來審查監督國安公署及其人員的行為的合法性?公署在執行職務時能否正確適用香港法律?若香港個人或組織的「合法權益」(人身權和財產權)受到侵害,能否在香港法院起訴國安公署獲得補償,抑或能否在內地法院起訴並獲得法律救濟?凡此種種,我們都希望獲得答案。在探索回答這些問題時,作為原則,我們應當秉承一個大前提:國安公署已經成為香港法治的特例,唯不能成為香港法治之上的特權。從國家建構層面觀之,這也是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大目標的應有之義。
(四)專屬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權
香港國安法第65條規定:「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按字面理解,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成為香港國安法唯一有權釋法者。這與基本法第158條規定的釋法制度大相徑庭,後者確立了香港法院經授權取得的對基本法(儘管並非完全)的解釋權。這就引出了兩個問題:其一,香港國安法的解釋權條款,緣何沒能沿用基本法的先例?其二,規定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對香港法院適用香港國安法,乃至延續香港普通法的司法傳統產生怎麽樣的影響?
基本法第158條是充分平衡與兼顧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香港普通法制度的產物。然而,回歸以來基本法司法實踐證明,第158條所確立的釋法制度與機制並不完善,全國人大常委會與香港法院的釋法權(以及承載權力運行的法律系統)之間存在著天然張力。第158條嘗試但沒能化解這種內在的矛盾與衝突,這在歷次人大釋法所引發的爭議中已可見一斑。其中,最突出的矛盾莫過於解釋權的歸屬及分配問題。香港國安法「一刀切」地將釋法權收歸全國人大常委會,可能正是基於對基本法釋法制度的反思與矯正。當然,或許有人會主張一種更簡單的解釋,那就是國家安全事務不屬香港自治範圍,參照基本法第158條的做法,香港國安法解釋權當然並且全然地歸屬全國人大常委會。然而,這種理解過於簡單化,罔顧香港特區與中央共享國家安全事權之制度安排,且置香港實行普通法司法制度這一事實於不顧。
按照普通法傳統,法律被制定以後,必須且只能交由法院去解釋與適用。香港國安法的安排徹底改變了普通法制度下香港法院對於法律解釋的獨佔性。只是法律解釋是司法活動的必然過程,從裁判庭到終審法院在審理國安犯罪案件必定涉及對香港國安法條文的適用與解釋。在「吳嘉玲案」中,終審法院重申,「法院的職責就是適用(apply)法律,為著適用法律,法院需要解釋(interpret)法律」。問題在於,法院解釋適用香港國安法的司法過程怎樣才能和「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這一新制度安排相協調?
香港國安法並未規定任何釋法機制或程序,這可能會成為混亂的根源:法院在審理案件過程中是否可以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什麽條件下會作出解釋?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是否有溯及力?全國人大常委會在過往的基本法釋法過程中,釋法程序的欠缺已頗受詬病,可惜香港國安法在這一點上却並無回應或改進。當然,這可能正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想達到的效果,即全面地、終局地掌握香港國安法的解釋權,不論是從釋法內容上,抑或從釋法程序上。
從實際出發,為了避免理論與實踐的混亂發生,我們可以把第65條理解為香港國安法的終極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這既可以維護國家主權者的最高權威和保留它的最後話語權,又可以維持普通法法院的運作秩序。與此同時,法院如想最大程度地保持自己的司法權威,則必須在司法適用中(至少反映在判决結果上)表現出對立法者更高程度的司法遵從(judicial deference)。
三、國家安全刑法制度與
香港刑事法律制度的協同與整合
(一)國家安全罪行與本地原有罪行的整合
儘管第23條立法在香港特區長期缺位,但這並不意味著香港缺乏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進行(直接或間接)懲罰的法律。例如,《刑事罪行條例》規定的「叛逆」「叛逆性質的罪行」「襲擊女皇」「煽惑叛變」「煽惑離叛」「煽動罪」,以及《公安條例》、《社團條例》、《官方機密條例》等也規定了為數衆多有關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的罪行(本文統稱為「本地原有罪行」)。香港國安法創設的四大新的罪行(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恐怖活動罪、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與本地原有罪行,存在著部分的重叠與競合關係。據此,我們實際面臨著處理國安罪行與本地原有罪行之間關係的複雜問題,這包括:其一,當某一行為同時涉嫌觸犯國安罪行與本地原有罪行,應當按照哪一罪行起訴?其二,國安罪行與本地原有罪行是否存在不協調或矛盾之處?如有,是否需優先適用香港國安法?其三,從法制統一與長遠發展的角度來看,香港有關國家安全的刑事法律不應當呈現為如此割裂的兩套系統,因而有必要整合(integrate)國安罪行與本地原有罪行,使之發展成為一套(a uniform)更新的、統一且兼容的刑事罪行系統。
(二)內地刑法及刑法理論對香港的影響
「一國兩制」與基本法將內地與香港的法律制度區隔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並不適用於香港。但回歸以來的經驗表明,內地的刑法仍有可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香港法律制度。其影響的路徑之一便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根據基本法第18條,將包含刑事法律的全國性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在港實施;此即全國性法律的「在地化立法過程」。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規定了侮辱國旗的刑事責任條款,被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後由香港立法實施,從而轉化為《國旗與國徽條例》中的罪行。同樣,《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後由香港以本地立法《國歌條例》的形式予以實施,後者規定的不當使用國歌的罪行、侮辱行為的罪行,也是對前者侮辱國歌的刑事責任條款的轉化。
按照與《國旗法》類似的路徑,香港國安法也將直接影響香港的刑事法律制度。頗為不同的是,後者包含更多更明確的罪行及罰則,因而影響範圍將更大;並且後者是通過直接公布而非本地轉化立法的方式實施,因而影響更為直接、程度更深。香港國安法的這一影響可以從兩個方面具體展開:從刑事立法上來說,正如前文提到,香港現行刑法與國安罪行有所交錯,因而需要進行修改或補充以適應,進而吸納國安罪行;從刑法理論上來說,國安罪行背後承載的是內地的刑法理論與刑法體系,香港執法與司法機構在辦理國安案件時,會否參考以法律意見(expert opinion)形式出現的內地的刑法理論與實踐?如參考,又將對香港的普通法系統產生怎麽樣的影響?就最後一點而言,有待香港司法過程和案例予以揭示。適時適當地考量國安立法背景、立法理據、相關的內地刑法理論無疑對完善香港國家安全罪與罰制度會有裨益的。
(三)國家安全罪行的執法者
香港國安法除了給香港的刑事法律制度帶來改變外,也重新定義了國安罪行的刑事執法者。特區警務處專設維護國家安全部門(「國家安全處」),作為警隊專門力量「調查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第17條)。但它却不是唯一的刑事執法者。按照第49條,國安公署亦有權「依法辦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這會否造成「二龍治水」的局面?回答這個問題,關鍵在於正確理解香港國安法對於國安犯罪案件的管轄權的規定。根據該法第40條,香港特區對本法規定的四大類犯罪案件(「四大罪行」,參見第三章「罪行和處罰」第20至35條)行使管轄權,但本法第55條規定的情形除外;第55條規定,在列舉的三類情形下,國安公署有權直接對國安犯罪案件行使管轄權。這也就是說,對於香港特區的國安犯罪案件,原則上、一般地由特區管轄,具體是由警務處國家安全處負責調查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律政司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檢控部門負責案件的檢控工作;在法定例外下,由國安公署負責管轄/調查,且國安公署的管轄不僅應當滿足第55條規定的三類情形之任一,還應當滿足第55條規定的程序條件,即經特區政府或國安公署提出,「並報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換言之,國安公署直接行使調查權,必須事前經過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方可行使,即必須滿足實體和程序要求。
因而,警務處國家安全處與中央駐港國安公署,雖然都具有刑事執法者的身份,但並不是同時生效的。在一般情况下,國安公署無權調查、追訴香港特區的刑事犯罪。
四、對現行香港刑事司法
與訴訟程序的影響
(一)香港國安法刑事程序在香港的實施
就國安犯罪案件而言,香港國安法的條款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香港既有的刑事程序,或引入全新的刑事程序。因而我們需要關注國安案件有關刑事程序在香港的落實。本文選取幾個具有代表性的刑事程序問題予以分析。
其一,保釋。香港國安法實施前後,保釋問題受到廣泛關注。立法實施前,不少媒體常使用「警察捉人,法官放人」指責法院未能有效懲治暴力示威者。香港國安法特別規定了國安犯罪的保釋程序(第42條),將香港既有法律中的「保釋為原則,不保釋為例外」改變為「不保釋為原則,保釋為例外」。通過「唐英傑案」、「黎智英案」兩件保釋案件的司法實踐,香港國安法下的保釋制度的適用已經逐步清晰。在黎智英案中,終審法院認為香港國安法有關保釋的規定,給香港既有保釋制度創造出一個特殊例外,提高了保釋的條件;判斷被告人能否獲得保釋時,須遵循兩步走,首先按照香港國安法的保釋條件予以判斷,照此條件如果可獲保釋,再放入香港既有保釋制度中檢視,最終得出結論。從該判决中可以看出,終審法院將香港國安法創設的刑事程序視為原有程序的特殊例外(而非平行或相排斥的兩套規則),從而吸納到既有制度之中。
其二、公開審判。法院向社會(包括新聞界)公開是普通法的一個基本原則,也是規定於《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公民基本權利,通過《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在香港生效實施。香港國安法對「公開審判」作了一些限制,規定「審判應當公開進行。因為涉及國家秘密、公共秩序等情形不宜公開審理的,禁止新聞界和公衆旁聽全部或者一部分審理程序,但判决結果應當一律公開宣布」(第41條第4款)。這一限制性規定與《香港人權法案》的限制性規定基本一致,並沒有對香港既有的公開審判制度作出實質標準的改動。問題在於,香港國安法並無規定哪一主體有權作出不公開審判的决定。從普通法的視角來看,這理所當然屬法院自治的事項。《香港人權法案》也規定法院有權决定之,《刑事罪行條例》、《官方機密條例》規定控方有權提出不公開審理的申請,决定權仍在法院。無論國安犯罪案件公開審判與否,判决結果都應當公開宣布。
其三、陪審團審判。在香港,陪審團審判(jury trial)並不是一項憲法性的權利,但作為普通法的傳統司法制度,有其憲法上的重要意義,這一點也為基本法第86條所確認。陪審團由適格的普通公民組成。由陪審團來决定罪成與否,有利於增强刑事審判的正當性與民主性,因而,有學者將其比作「一個小型的議會」(a little parliament),也有學者將其譽為「自由對抗暴政的象徵」(a symbol of freedom against tyranny)。綜合世界各國實踐來看,進一步適用或實施陪審團審判是潮流趨勢。回歸以來,香港社會也多番討論提議將陪審團制度適用範圍擴展至區域法院。
然而,香港國安法第46條反而限縮了香港陪審團審判的適用,對高等法院原訟庭審理的國安犯罪案件,「律政司長可基於保護國家秘密、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或者保障陪審員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等理由,發出證書指示相關訴訟毋須在有陪審團的情况下進行審理」。這種安排的合法性或正當性為何?國安犯罪案件大多是政治敏感類案件,排除陪審團審判有失民主性的外觀,可能招致更多非議。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03年保安局提出的國家安全立法草案中,特別提到涉國安犯罪案件將由陪審團審理。此外,將排除陪審團審理的决定權交給律政司長(在此情形下即政府)是否恰當?香港既有法律中有關陪審團的職能能否全盤轉交給法官受理?
然而也應看到,排除陪審團審判也有毋庸置疑的合理性,也許可以以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為理據予以解讀。不可否認,法律確立的新做法勢必受到理論與實踐的雙重挑戰,需要結合實踐進一步認真研討。
其四,國家秘密的認定。香港國安法有多處條款涉及「國家秘密」的認定。國家秘密的認定將直接影響或關涉到:(1)「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的認定(第29條);(2)决定審判是否應當不公開進行(第41條第4款);(3)决定高等法院原訟庭審判是否應當在無陪審團的情况下進行(第46條);(4)相關人員的保密義務(第63條)。可見,國家秘密的認定兼具實體與程序上的重要意義。香港國安法第47條將認定國家秘密的權力交予行政長官,規定「法院在審理案件中遇有涉及有關行為是否涉及國家安全或者有關證據材料是否涉及國家秘密的認定問題,應取得行政長官就該等問題發出的證明書,上述證明書對法院有約束力」。這一規定與基本法第19條的規定頗為類似,後者明確了法院對國家行為無管轄權,因而對相關事實問題應取得行政長官的證明文件。香港國安法對國家秘密的認定也作類似要求,那麽我們是否可以倒推認為,法院對於國家秘密的認定亦無管轄權?如果是,那麽將國家秘密的認定排除於法院管轄之外,能够找到基本法或法律上的依據嗎?
落實這一規定,同樣面臨實體與程序上的難題:在程序上,如法院不提出,行政長官可否主動發出證明書?證明書對法院有約束力,是否意味著法院對國家秘密的界定毫無審查空間?法院對行政長官發出證明書的行為是否有審查權?在實體上,行政長官認定是否屬國家秘密將遵循何種標準?按照「法定原則」(prescribed by law),應當存在具體的成文標準以避免行政長官在個案中創設標準。現時香港《官方機密條例》中將「保安及情報資料」、「防務資料」、「關乎國際關係的資料」、「關乎犯罪及刑事調查的資料」、「因諜報活動所得的資料」等類型的資料作為機密予以法定保護。行政長官對國家秘密的認定,是否將依照或參考香港本地成文法的標準?抑或,行政長官會否遵循或參考內地法律中有關國家秘密的定義,或者接受中央政府的認定國家秘密的指令?
行文至此,可以提出如下問題:立法者在制定香港國安法關於保守國家秘密規定時,是否參照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而後者關於「國家秘密」的定義看上去是很寬泛的。內地學者王錫鋅教授認為,有關國家秘密的定義及範圍過於寬泛,甚至包括「經國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門確定的其他秘密事項」。如果要求香港法院套用上述全國性法律的定義,可以預見將會有可觀的國安案件排除陪審團、不予以公開審理。就這一點來說,香港特區不應當將內地有關國家秘密的認定標準直接引入本地。
(二)「內地管轄」激活後的有關刑事程序
前文談到,香港國安法第55條列舉了三類特殊情形,在該等情形之下,國安公署有權直接對三類國安犯罪案件行使調查權,並將由內地司法機構適用內地刑事程序法管轄案件。這種做法勢必影響到當事香港居民的權利。因此我們有必要關注「內地管轄」激活後的刑事程序的特點與可能出現的問題。
其一,指定司法機關。在內地的刑事程序體系中,偵查、公訴、審判的職能一般分別由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所承擔。按照香港國安法第56條,「內地管轄」激活後,國安公署負責立案偵查,具體公訴者與審判者則是不確定的,需要由最高人民檢察院與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有關」檢察院與法院。「反修例運動」已經證實,香港居民對內地的法治水平與司法公正缺乏必要了解,甚至表現出頗多不信任。因而,指定司法機關既要考慮到地域、語言等因素以方便刑事程序的推進,更要考慮到當地法治水平、法官素養與專業水平、城市形象(比如更為港人所熟知)等因素,既保證案件公正處理,同時可以打消港人顧慮。指定司法機關的决定也應當由最高人民檢察院與最高人民法院儘早地、公開地作出,並對指定理由進行說明。也許珠三角地區(如深圳或廣州)司法機關更適合於被指定。
其二,犯罪嫌疑人與被告人的辯護權。香港國安法第58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自被國安公署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這與中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是一致的,明確了立案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即有權委托辯護人,但將辯護人的身份限定於律師。那麽香港的國安犯罪嫌疑人是否有權聘請香港的律師?法律文本語焉未詳,尚待有權機關發出指引。事實上,無論犯罪嫌疑人聘請的是香港抑或內地律師,均會面臨跨越兩地的地理障礙、代理與辯護技術障礙和法律知識障礙,特別是代表兩個不同法域的法律知識方面的障礙。另外,中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在偵查期間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許可」,那麽國安犯罪嫌疑人的律師會見當事人,是否也需要經國安公署的許可?若類推,前置許可將會是必要的。香港國安法第5條第2款原則性規定,「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於是我們應當進一步思考,如何切實保障犯罪嫌疑人與被告人(尤其在內地管轄的情况之下)的辯護權。
其三,作證義務。香港國安法第59條規定,「內地管轄」激活後,「任何人如果知道本法規定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情况,都有如實作證的義務」。這一規定也給我們留下了一些疑問:首先,這裡的「任何人」的範圍是否存在限定?特定身份的人可否得到豁免?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身、外交人員、配偶父母子女等親屬,這就涉及拒證權制度的研究。其次,如果證人拒絕出庭,內地法院可否采取强制手段,以及强制手段如何實現?對於拒不履行作證義務的人又當如何處理/處罰?最後,「如實」的作證義務如何確保?有很多情况都可能導致證人無法「如實」作證,例如證人虛假陳述或隱瞞實情,以及其他人威脅、賄買證人等等。違背「如實」將會產生什麽樣的後果與責任?鑒於如實作證義務是强加在「根據本法第55條規定管轄案件時」,是否意味著該規定不適用於香港特區在特區內對本法規定的不屬第55條情形的其他犯罪案件行使管轄權時?如果是,是否意味著可以徑直適用香港現行刑事司法制度與原則?
由內地司法機關適用內地刑事程序法律管轄案件,也有可能導致內地刑法的擴張適用。這主要是指,香港居民或外國人參與到內地管轄的國安犯罪的刑事訴訟之中,即處於中國《刑法》的屬地管轄(territorial principle)之內。例如,在「內地管轄」情况下,香港居民在國安犯罪案件中作僞證,便觸犯了中國《刑法》的僞證罪(第305條),將受到內地刑法的管轄,被內地公訴機關追訴。
結語
全國人大常委會為香港特區制定香港國安法,並迅猛有力地在香港施行,引起了區內、國內和國際的廣泛關注,其中贊揚支持者大有人在,批判聲音也不絕於耳。本文完全從憲法、基本法和刑事司法角度檢視香港國安法對香港特區法制以及司法制度可能帶來的直接和長遠影響,旨在發現問題,並找出理論上邏輯自洽、對實踐可能有啓發意義的答案。
香港國安法以中央立法方式完善香港特區國家安全法律制度,促成特區履行其維護國家安全的憲法義務,為維護特區國家安全提供堅實基礎,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與政權安全提供保障。但我們同時也要看到,新法對香港特區原有的法律體制與司法制度帶來了一定程度的衝擊,其在地化將會是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其實施過程也必定會提出新的問題。為此,我們應該未雨綢繆,在憲法與香港基本法前提下以主動、進取的態度應對,開展理論探索,提出切實可行的策略,從而保證「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本文接上期內容)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1年9-10月號第28-37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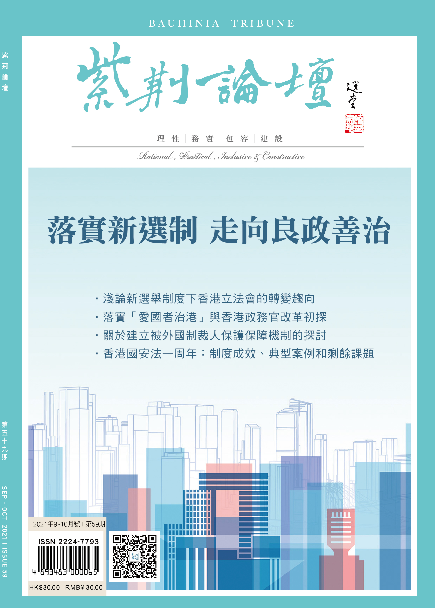
掃描二維碼分享到手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