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宗城
時隔14年,王朔再度出新書,這個事情本身就足以構成一個文化現象。
王朔如今已不再是時代的弄潮兒,但在上世紀90年代,他是中國內地最流行的一位作家。他的《動物兇猛》被姜文改成了《陽光燦爛的日子》;由他編劇的《編輯部的故事》開啟了中國情景喜劇的春天;馮小剛從他那兒拿過來不少點子;他和徐靜蕾的故事曾被全北京的媒體嚼爛舌根;他的小說《過把癮就死》《我是你爸爸》《看上去很美》《永失我愛》等,成為了一代人的青春記憶。
老舍之後,王朔可能是最能代表京味文學的作家,儘管他的作品在文學價值上仍然存在巨大爭議,但很少會有人否認他對一代讀者和寫作者趣味的深深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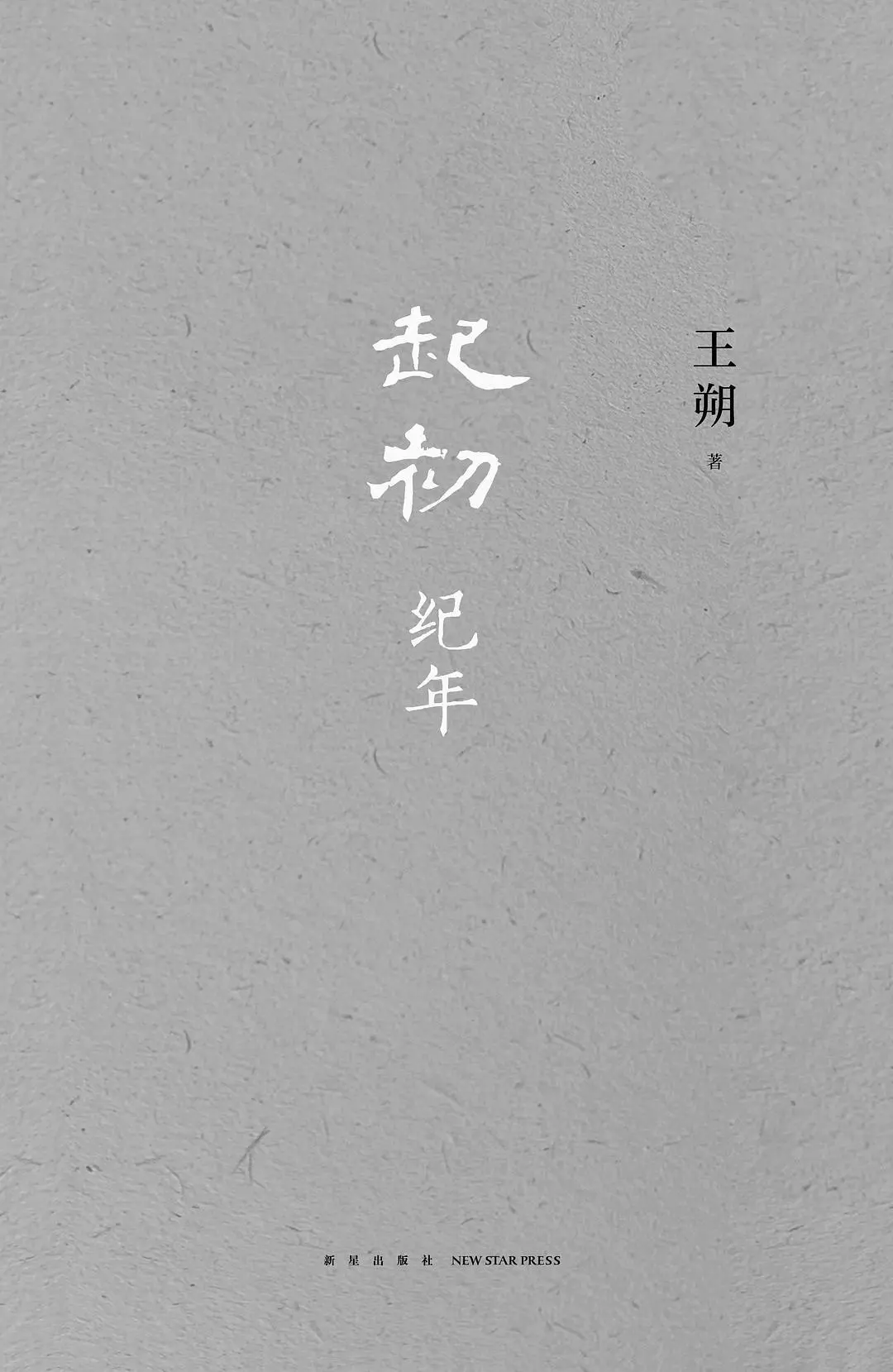
一、《起初:紀年》:依然“王朔味”的小說
《起初》四卷本是王朔這輩子寫得最長的書,也可能是封筆之作。王朔在《起初:紀年》的自序裏說:“這本書開筆於本世紀初葉,原計劃三年完成,後來一猛子紮出去,再擡頭就是十啦年之後,街上流行戴口罩。”
這部140萬字的小說分為《魚甜》《竹書》《絕地天通》《紀年》。四卷本小說,從中華文明的源頭,到漢武帝頒布罪己詔為止,意在“起大妄,上探我國文明源頭”。
之所以最先出《紀年》,是因為王朔和和編輯討論後覺得,《紀年》“文字最順,閱讀體驗最好,而前數卷趣味、用典、用辭則多有可商榷”。
那麽,這本《起初:紀年》到底寫得怎麽樣?王朔為什麽時隔十四年那麽長,寫起了漢武帝時候的故事?他為什麽會覺得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咱們敞開天窗說亮話——這本書就是王朔眼中的《史記》,是他的童年、他的青春、他人生世界觀和的價值觀最重要的落腳之處。
這本書為什麽不停地寫漢朝的戰略部署、漢朝和匈奴的對峙,寫漢武帝和群臣的韜光養晦到出擊漠北,及至李廣悲劇、司馬遷的隱痛、漢武帝晚年對人生的回望,以及整個漢家朝廷從戰爭時期到休養生息的轉型?這些事件投射在王朔心裏,實則地喚起了他的成長記憶。此中的歷史與現實互文,或許才是王朔的抱負所在,他想寫出一部屬於自己的《史記》,他要從上古寫到漢朝,為一代人的光榮與暗影留下一份隱秘的見證。為此,這一次他投入了自己最大的進取心。
這本書表面上看,其實是按照通鑒紀年——漢武帝年少時,到後元二年漢武帝駕崩——把漢武帝一朝的大事小事走了一遍,串聯起漢朝半個世紀的波瀾壯闊。期間阿老、田蚡、竇嬰、東方朔、司馬遷、李廣、衛青、霍去病、李陵、桑弘羊、戾太子、劉弗陵等重要人物都有登場。其中,貫穿全書的兩個人物是漢武帝和司馬遷——一個是皇權的代表,一個是知識分子的代表。
這體現了王朔的整體立意:他就是要寫一部涵蓋君主、文人、武將、外族、宦官、外戚、宮闈、諸侯王和江湖人士的書,要把自己對於中國政治、歷史與文化的理解融匯在這本書裏。換言之,王朔要在這本書裏自問自答的是“中國何以成為中國”的問題,是中華文明如何形塑自身特殊性的問題。
理清楚這層,不妨就來看看王朔這一次的完成度怎樣,進而歸納幾個這本書明顯的優缺點。
首先需要說明,如果是想看歷史非虛構或者微觀史學著作的讀者,最好還是放低對王朔這本小說的期待,不然開篇洋溢的北京話就會讓你納悶,這到底是西漢故事,還是北京胡同老大爺跟你嘮嗑?王朔這部小說最具特色也最可能引發爭議的就是他的語言,他在用自己改造後的北京白話潛入歷史,在歷史故事的基礎上徹底過一把文體遊戲、語言風暴的癮。
這部小說把王朔的“碎嘴”發揮到了極致,試舉幾例:“我漢鄉下不識字的人也是這麽數日子,今天出門倒黴,今天出門不倒黴,把倒黴事兒挨著過一遍就一年了。”又比如這句有點俏皮感的:“阿老,求心疼,用咱聽著不鬧心正經漢語。”
與此同時,王朔在文中,還混合其他方言、結合文言文,創造了許多新的語言實驗、比如七十七章最後兩句:“上終日獨坐,繞膝、坐膝皆貓咪,撫貓若撫幼子。囁嚅自語人皆不解其意,惟貓知。”明顯是“文言腔”的表述。又比如說全書最後一段節選:“其實全無動於衷,再追憶難過亦幹涸。由是可知情感為世間物,一世情一世了,人格秒刪,對象亦空置,戀怨無所寄。”
至於王朔這麽用語言是不是好,是否適合用以重述漢朝故事,這需要由時間檢驗。但從創造的角度來說,其實《史記》《漢書》乃至後世史學著作已經就這段歷史說過很多了。王朔沒有“中規中矩”,而是用一種借古喻今、故事新編的手法,帶領讀者進入一場怪異的體驗,這或許還算不上傑作,但至少有新意。
可以說,語言是這本書最大的特色,它仍是具有“王朔味”的一本小說。
第二個明顯的長處在於此書的收尾。這本書後面比前面寫得好。前半部中,王朔像是一股腦泥沙俱下地來了一盤歷史故事大亂燉,對於歷史素材的使用上難言精妙,未見作者的精心剪裁,部分章節讀罷仍有堆砌之感——出場人物多、事件多、敘事者又嘴碎,特別喜歡拉家常、講戰略部署。刻薄一點說,就是五個不停:“不停打仗、不停戰略部署。不停男人嘮嗑、不停人事流轉、不停發生外憂內患”。這導致行文拖沓、滯重,若非作者是王朔,有多少讀者真的能耐心讀下去,其實是一個問題。
然而到了後半部分,當王朔寫到李廣、李陵父子遭遇、巫蠱大案,寫到漢武帝寫《輪台詔》時,卻更加沈郁、凝練,也更具有一種“人間滄桑”之感,讓小說的質感更渾厚了一層。這也許和王朔人到暮年的生命經驗有關——世事終究浮沈寂滅,漢武帝一代雄主,晚年終究也逃不過昏聵、懺悔與孤獨的命運。
二、帝王故事裏沒能回避的缺點
與此同時,王朔此書還有一個缺陷無法回避。
王朔以漢武帝為主角本身並無問題,但如果過於沈溺於君主的心理世界,對於帝國的武功愛慕有余而警醒不足,將民間疾苦視作一種帝國風景的邊角料的話,一本小說的穿透力就會打折扣。
比如《哈德良回憶錄》也寫君主,作者尤瑟納爾寫的就是羅馬“五賢君”之一,但她不是平鋪直敘地展現皇帝的一生,而是把敘事的“現在時”設定在皇帝罹患心臟病的晚年,通過詩意而悵惘的回憶建造起一座歷史的紀念碑。這座紀念碑的重點已不是皇帝功績,而是對於人類命運的追思,對於個體意志、欲望、身份與所處環境沖突的描繪,乃至對於個人內心世界卑劣一面毫不掩飾的暴露。這些使得尤瑟納爾這本《哈德良回憶錄》區別於歌功頌德的流水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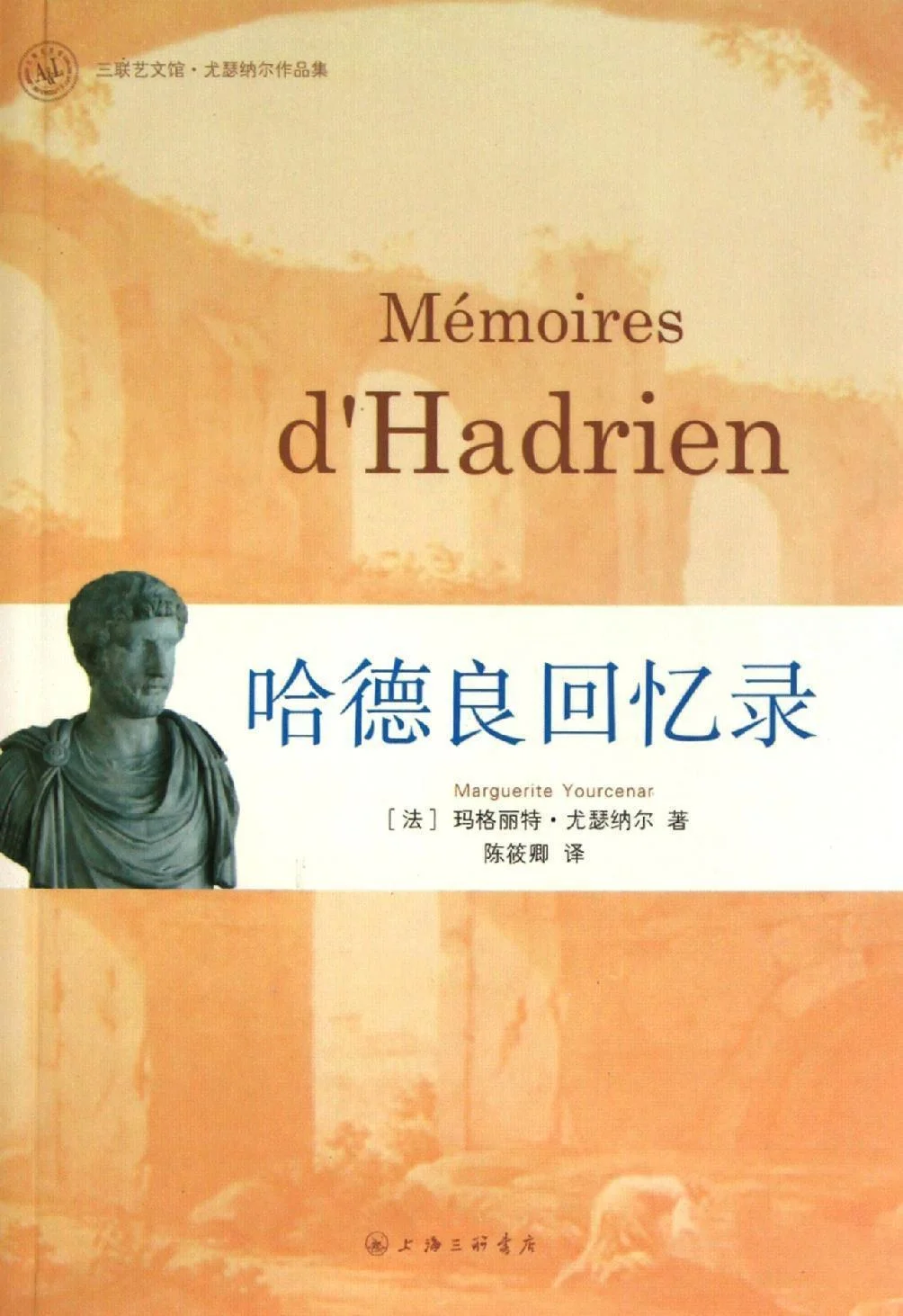
相較而言,《起初:紀年》多戰爭籌劃、宮廷政鬥、江湖逸聞,卻對武帝時期連年征戰導致的勞民傷財著墨較少。
漢武帝在位54年,有四十多年都在和匈奴等國打仗,期間遠征人數動輒數萬,十數萬,這還只是前線士兵數量,再考慮到後方轉運、補給部門,漢武帝時期投入一次大規模戰爭的人數,超過百萬不在話下。
連年征戰,國中疲憊,到了武帝末年,全國人口較漢初直接減半,民間暴動也頻頻發生。若非漢宣帝勵精圖治,漢家後人在休養生息和開疆拓土之間找尋平衡,漢武帝恐怕既要成為開疆拓土之雄主,也要成為點燃民眾怒火的眾矢之的。
不過說到底,我不覺得王朔在歌頌漢武帝、重覆陳詞濫調,但他的歷史意識本可以更深入,本可以在歷史剪裁、敘事手法、人物內心世界勘探的層面上,對自己更狠一些。這是一個完成度的問題,我並不懷疑王朔的野心和努力,但他更深的立意在漫長瑣碎的敘事中深陷於迷霧,他在用北京白話解構傳統歷史書寫的同時,並沒有讓我看到一個更有創造力的東西。王朔在做的東西,和多年前“新歷史主義”在做的、王小波在做的(例如他寫《紅拂夜奔》),其實殊途同歸。但王小波至少在批評烏托邦幻覺、苦難敘事、民粹主義後張揚理性和自由的可貴,提倡一種審慎的、基於理智與共情的人生的態度。王朔解構後捍衛的是什麽呢?這其實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三、王朔:一個夾在反抗和迎合中的人物
很多讀者閱讀《起初》,沖的是王朔的名頭,但今天的年輕人可能已經不太理解,王朔對上一代人為什麽有那麽大的影響力?為什麽說他是一個九十年代標志性的文學人物?

王朔本名王巖,滿族人,出生南京,祖籍遼寧鞍山,大院子弟,在他出生那一天(1958年8月23號),金門響起炮火聲,解放軍福建前線部隊正在對據守金門島的國民黨軍發動猛烈炮擊,國民黨軍亦做出反擊。按他自己的說法:“我出生在八二三炮戰這天。按迷信的說法,不知有多少冤魂托身,小時候不覺得,四十以後發現臉上帶著一股戾氣。”
王朔說話直接,有孩子氣,他擅長寫小時候經歷過的事、寫通過孩子眼睛看到的世界,是以文字中頗有君特·格拉斯《鐵皮鼓》的荒誕意味。
他盛年時嬉笑怒罵,甚至化用別名批評自己,但骨子有一股柔情,對於至情至真之人,他有惻隱之心。王朔是個正經人,但他要用不正經來包裹他的正經。有一類人本來不正經,要裝作正經的樣子,這類人很多,王朔要面對的就是這類人,他要用自己的筆,來戳破那些道貌岸然和裝腔作勢,所以他一度把自己活得“特別能戰鬥”,成了文壇“壞小孩”的代表。
王朔並非孤軍奮戰。他在文學界中不乏擁躉。風頭正勁時,王朔在《鐘山》《收獲》《花城》《人民文學》等刊物都發過小說,如果他真是一個人和主流文學圈對著幹,就不會有“王朔現象”的出現。
某種意義上,王朔才是九十年代的主流,他代表一種無法壓制的聲音,那就是把假模假樣的東西從台上拉下,將事物還原成本來的模樣。誰也別裝孫子,站著的就是個人。
許多批評家說他俗,市場卻歡迎他。在上世紀末,王朔是中國最炙手可熱的寫作明星和編劇,九十年代乃至本世紀初的幾部現象級影視作品,比如《編輯部的故事》《我愛我家》《非誠勿擾》等,都跟王朔有關。
如果要為中國1990年代選一位代表性作家,綜合文學功底、影響力、象征意義,王朔也是不可忽略的人選,因為,他真切地影響了一代人,掀起過一場反思語言和價值體系的風潮。
此前友人問我,王朔和王小波是同時代人,兩個人都具有反抗氣質,但為什麽給人的感覺截然不同?解題之處在於出身和成長環境。
王朔是大院子弟出身,所謂“紅旗下的蛋”,從小對衛國守邊的軍人生活耳濡目染。之後,他經歷文革和改革開放。可以說人生的前三十年,王朔經歷了兩次天翻地覆,“根正苗紅”所帶來的優越感在時代中慢慢磨成了五味雜陳。說他是“痞子文學”、擁護商業,或者說他與主流保持一種曖昧、說他其實是“假反抗”,都有道理,但不夠詳盡。
王朔的一只腳留在計劃經濟時代,另一只腳又踏在改革開放的土地上,享受著市場經濟的紅利。他在生存經驗上受惠於“公家”,他的成功經驗中,又有對“反抗權威”、“親近民間”的九十年代話語的巧妙利用。他把崇高打倒在地,自己卻沒有能力建立新的價值坐標。於是,讀他的文字很過癮,但過癮完了又茫茫黑夜空落落。讀他的作品,會感到失去了什麽,但又沒有重建什麽,那是一種未完成的中間狀態。
王朔是一個九十年代的寵兒,那時候他的“叛逆姿態”很新。但邁入新世紀,在全球化和市場經濟成為定局以後,王朔依然有名,只是已不再是弄潮兒和先鋒者。王朔2007、2008年出版的作品《致女兒書》《和我們的女兒談話》,口碑明顯沒有之前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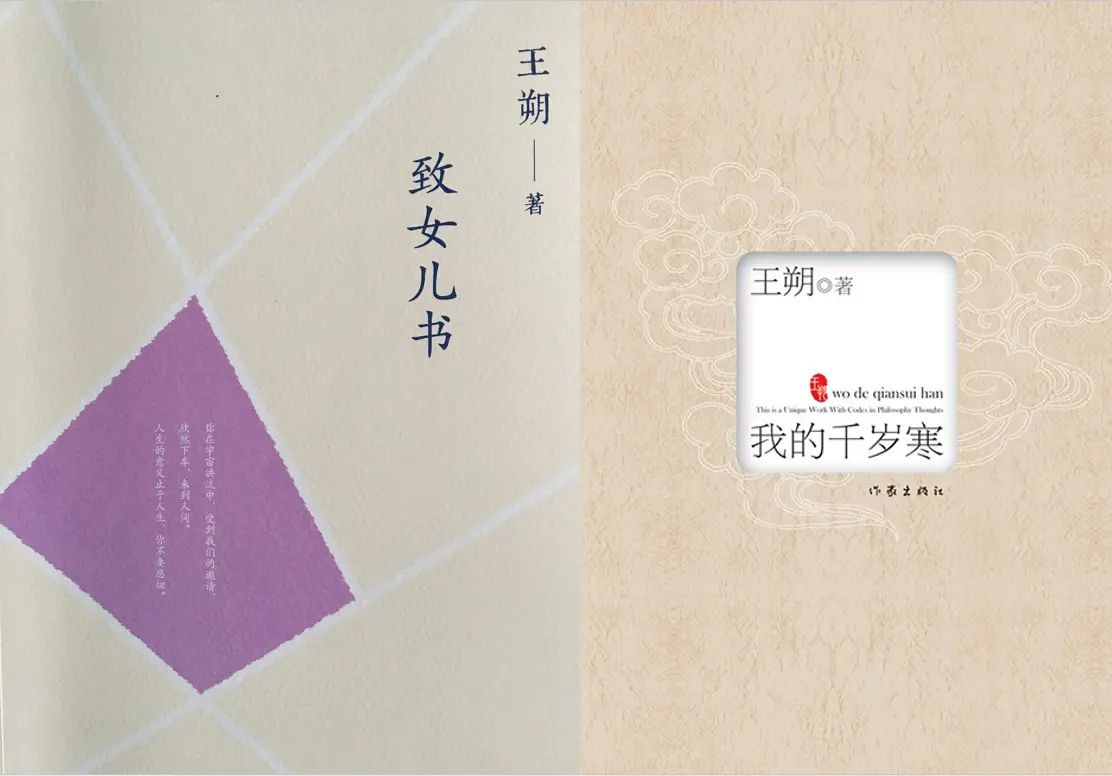
當一個個“小王朔”搶班奪權的時候,王朔依然有執著。他需要一個交代,一個給自己文字生命的交代。無論是《看上去很美》《致女兒書》還是《新狂人日記》,都擔不起這份重量,但一百四十萬字的《起初》可以。這就是王朔的執念。
四、王朔真正的價值和局限
九十年代王朔的真正貢獻在於:第一、他對北京白話的創造性使用。使得北京白話在老舍之外,有了另一種進入文學的方式,這在當時是革命性的和創造性的;第二,他激勵人們重新思考藝術內部的分界。通俗文學一定就低人一等嗎?影視劇是否能成為藝術?又是誰人為制造了雅俗之分?王朔持續在用小說和影視劇創作推動這個議題,他的小說不被一些純文學愛好者認同,但他又是能代表九十年代精神氣質的一位作家,而他在中國影視劇發展中的作用、分量更不必說。未來,王朔在影視劇史上的地位,或許更高於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至於說王朔作品中“反抗權威”、“親近民間”的精神、姿態,其實他的身份和所得決定了,他很難構成真正的反抗。過了“動物兇猛”的階段,人會變得柔軟,不只是追憶“陽光燦爛的日子”,也是知道那“看上去很美”的東西,終究有冷暖自知的成分。
王朔不是變保守,他只是知道九十年代的姿態已經不合時宜。王朔是一個擅於解構卻無法建構的人。他曾經與一切看不順眼的東西為戰,但他擁抱的那些——娛樂、商業、消費主義、民粹傾向,現在都已經成了潮流。在這種情況下,繼續故作姿態只能是一種撒嬌。
當王朔離開時代浪潮,從以他本人命名的時代符號中抽身而出,他更像是一個退隱者和本分的寫作者。骨子裏,王朔知道自己的軟弱,在《致女兒書》《我的千歲寒》中,他甚至毫不掩飾這種軟弱。那脆弱讓人傷感,讓人喜歡,卻也讓我們更意識到他的局限。
在新作《起初:紀年》中,王朔看起來變了,但你發現那個內核其實並沒有變,他只是換了個時空。小說裏不斷出現的北京白話、拉家常的氛圍、對於英雄悲劇的追緬、對於死亡的思索等,其實仍是王朔的舒適區,也跟他的生活密切相關。
所以,喜歡王朔的讀者會很喜歡這部作品,不喜歡的就會覺得又臭又長。因為在書中,我們看到的其實是一個活在90年代的憂傷影子。他越是熱情地跟我們講述,我們就越嘆息,因為我們看到了一個人註定被他的時代封印。而這,幾乎是大部分寫作者的宿命。
五、了卻了汪曾祺的一個心願
最後,不妨說一段題外話。在王朔寫漢武帝之前,其實汪曾祺也計劃寫一部名叫《漢武帝》的長篇小說。
文學季刊《新文學史料》2020年第一期有一篇文章,名字就叫《汪曾祺未竟的“漢武帝”寫作計劃》(作者徐強)。文中介紹:“他(汪曾祺)有一些系列作品的寫作計劃完成了,但還有若幹計劃則因種種緣故沒有實現……長篇小說《漢武帝》的寫作計劃屬於後者。”
據說汪曾祺為寫《漢武帝》醞釀了十五年。他對漢武帝本人有著濃厚的興趣,這倒不是因為他熱愛這位皇帝,而是因為在汪曾祺眼中,漢武帝是一位“變態心理學”的代表,他的一生既是一部命運史詩、悲劇小說,也是對“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高度概括。
汪曾祺不是一位犬儒主義者,他只是一位清醒的“後撤步大師”,當你以為他“歲月靜好”的時候,他其實在琢磨如何用婉轉的方式,為過往遭遇的荒誕留下一份見證。所謂古人,無非假托言今的手法。
汪曾祺熟讀《史記》《漢書》《後漢書》,對漢代樂府熟讀成誦,他寫漢朝該是活色生香、別具一格的,但可惜直到汪曾祺去世,《漢武帝》終未面世。王朔和汪曾祺文風截然不同,但他們曾身處同一片天空,感受過時代變幻的寒與熱。王朔寫漢武帝,或許不是為了歌頌漢武帝,而是寫下一種長久發生在中國的命運。
作為人至暮年,棋手終局的作品,這本《起初:紀年》能否再度喚起新青年的感動?也許,這一次王朔打了一場漂亮的“敗仗”,他的語言風格和精神氣質一如既往,而他與時代的矛盾仍沒有得到化解。但至少,比起許多早就罷筆的同代人,王朔的沖鋒已經足夠壯麗。
掃描二維碼分享到手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