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記者 張清語 李天源
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本刊記者近日走訪部分香港抗日老戰士及其家屬,冀以歷史細節留存香港抗戰的珍貴記憶。曾經的港九大隊“小鬼通訊員”、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游擊戰士聯誼會會長林珍及“香港抗日一家人”羅氏家族後人黃俊康在接受本刊專訪時,講述了那段烽火歲月中香港同胞的家國擔當。
林珍:
8歲小通訊員傳遞“火柴棍”密件

受到家人的啟蒙,愛國之心與家國情懷早已根植在童年時的林珍心中。1937年抗戰爆發後,林珍的姐姐林展創辦刊物、參與賑濟活動等,於194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從事地下工作,在日、台軍人寓所做洗衣女工,期間因拒絕一名日本軍人調戲,惨遭誣陷,被日本憲兵打得全身青腫。林珍告訴我們:“姐姐那時候絕對不低頭的形象,對我產生了很深刻的影響。”林展通曉英語,於1942年成為港九大隊國際工作小組的主要成員,並於1945年任敵工科科長。抗日戰爭結束後,1946年,林展先後擔任北平軍調部第八執行小組中共代表方的譯員及北平軍調部中共代表葉劍英的英文秘書。
1943年,8歲的林珍與母親、哥哥參加了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一到游擊區,只有大概一周的時間進行準備,然後就正式開始戰士的生活了。”林珍當時仍與母親同住,但早晨軍號一響,就要和部隊一起出操,唱《三大紀律八項註意》,“雖然每天出操跑步的時候,我站在(操場)裡邊最小的圈裡,他們可能跑兩圈、三圈,我才跑一圈,但是也要跟著步伐一起走,那種馬上要投入集體戰鬥的氣氛,對我來講影響是很大的。”
最開始,林珍被分配了通訊員的任務,“通訊班的班長大我七八歲,也只有十幾歲左右的模樣。”每次去新的地方送信,當時的通訊班班長都要帶著她走第一遍,一開始是一個小時以內,後來距離慢慢加長,一路上需要經過哪些水溝、山坡、村莊,班長都會給林珍做記號。目的地交通站的名稱、站長名字,接頭時要講什麼話,都交代得清清楚楚。“那些密件像火柴盒那麼小,捲起來像火柴棍,每次運送二至三個,藏在腰間、褲頭。當時的任務執行得很順利,老鄉們也非常支持我們,我們什麼也不害怕。”傳遞情報之餘,林珍也幫忙印刷油印宣傳品。“一整天總是沒有閒著的時間,也因為自己能完成作為一個戰士的任務而自豪。”
1944年,因戰事愈發激烈,林珍與母親被調至傷兵醫院(戰地醫療所)工作。“所謂醫院,其實也只是大一點的寮屋。”林珍負責照顧傷員,後來也進行護理工作。當時醫院的物資十分緊缺,“用過的藥棉和棉紗不能丟,都要收集在一個籃子裡,然後我們這些小護士拿到河邊清洗,洗乾淨後再晾曬、消毒,重新利用。”到冬天,因長時間泡在冷水裡,林珍的手生了凍瘡,“當時癢得刺撓,媽媽整個晚上給我搓,怎麼搓也好不了。”被老鄉知道後,給林珍煮了蘿蔔水,等水溫降下來後把手浸在水裡一直搓,慢慢地就痊愈了。“生活在游擊區,跟大家在一起,什麼難處都不怕。”
在傷兵醫院中,如麻藥等基本藥品也十分缺乏。一些中彈的戰士經常在手術的時候沒有麻藥用,“那喊疼的聲音就像刺到我們心裡頭一樣。”手術中的傷者喊叫得口乾舌燥,林珍就用沾濕的棉布給他們潤濕嘴唇。“但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等戰士們的傷口好一點,他們就申請要回部隊、繼續戰鬥。”林珍亦曾協助救助在安裝地雷時被誤傷導致雙目失明的藍天洪和曾九,直到現在也仍舊與他們的後代保持著密切聯繫。
1995年,林珍重新聯絡上了當年的老戰友,投入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游擊戰士聯誼會的工作。“前輩們流的血換來了現在的和平,但現在的世界並不完全平安。要敢於保衛和平,才能永享和平。”
黃俊康:
“抗日一家人”是親人更是戰友

對家國的真摯情感,寫就了“香港抗日一家人”羅氏家族的抗戰史詩,羅氏家族的後人黃俊康亦為建設“香港沙頭角抗戰紀念館”作出卓越貢獻。在羅氏家族中,羅雨中、羅汝澄、羅歐鋒、羅許月及其配偶等11人曾參與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香港抗日戰爭。在戰爭裡,他們既是血脈相連的親人,更是並肩作戰的戰友。
國家的命運牽動著家族與個人的命運。羅氏一族為巴拿馬華僑,羅雨中、羅汝澄、羅歐鋒都是當時香港的高材生,“我大舅羅雨中高中畢業後在香港的洋行學做生意,二舅羅汝澄在念大學一年級,三舅羅歐鋒在讀高二。”據黃俊康回憶,因為自己的外公當時身體不好,三個舅舅已辦好護照,準備去巴拿馬接手家中生意。隨著抗日戰爭爆發,南京大屠殺等慘烈消息傳到香港,“他們看到了這些消息,於是開始參加抗日救亡活動”。香港淪陷前,羅雨中在香港從事地下工作,羅汝澄、羅歐鋒到內地參加抗日游擊隊,日軍進攻香港後,羅雨中擔任第一支抗日自衛隊“南鹿人民聯防隊”首任隊長,羅汝澄擔任過沙頭角中隊、西貢中隊中隊長和港九大隊副大隊長,三舅羅歐峰是海上中隊中隊長。母親羅許月則是港九大隊大隊部交通站站長。黃俊康告訴我們,在抗日戰爭結束以後,一家人過了一段時間和平的生活。1946年解放戰爭開始,他的長輩們又按組織的要求,到內地參加解放戰爭,並參加了新中國的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攻堅。“他們百折不撓、堅守信念的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永遠是我們的榜樣。”
曾為羅氏家族祖宅的羅家大院,以羅家後人出房和出相當比例的資助,已於2022年作為“香港沙頭角抗戰紀念館”揭幕,並向公眾開放。黃俊康告訴我們:“2017年,羅氏後人從世界各地回來祭祖,一致決定將祖宅讓出來作抗戰紀念館。”因為祖宅不能當、不能賣、不能捐,所以最後決定將其以每年一港元的象徵性價格永久租出。在香港廣州社團總會牽頭下,總共籌集了兩千多萬捐款,歷時五年,用民間的力量建成了香港第一個抗戰紀念館。黃俊康廣泛參與紀念館的設計、收集、籌建、運營管理等工作,“我曾與雕塑團隊多次討論紀念館門口的雕塑,希望雕塑能夠反映港九大隊的特點:首先是知識分子較多,所以雕塑中的機槍手是戴眼鏡的,這是我提出來的。他拿的機關槍是從日軍那裡繳獲的歪把子機槍。女戰士們在港九大隊發揮了重要作用,所以雕塑人物裡也有女戰士。港九大隊還有個特點,小鬼多,大部分是12 歲到15 歲左右的交通員,所以雕塑中也有少年的形象”。
“以前,一些香港人說,從不知道香港有這麼英勇的抗日隊伍。”黃俊康提到,“兩年多來,即使沙頭角地處偏僻,紀念館仍接待了將近9萬的參觀者。”這讓他覺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那些曾被淹沒的歷史,終於通過社會各界的努力,重新回到了公眾視野,可以為社會盡責,為前輩們盡孝。採訪中,回憶起與父母、親人共處時的點滴,已逾古稀之年的黃俊康忍不住落下眼淚。“我想告訴他們:你們的犧牲、拼搏,終於開始在香港被人認識和重視了。”
採訪的最後,黃俊康告訴我們,他幼時身體不好,母親曾向他講過“鐵沙梨”的故事:鐵沙梨是港九獨立大隊裡一個十四五歲的交通員,在一次戰鬥中,日軍包圍了他所在的游擊隊,他受傷後滾下山坡,連滾帶爬走了五六公里山路才找到交通站,到了站就暈了過去,交通站的人立刻將消息轉送總站,各部隊隨即做好應變準備。“鐵沙梨”這個名字源自廣東一帶的沙梨:每棵樹上總有幾顆硬得像鐵、摔不破的果子。講述抗戰故事,就是在延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那些曾在硝煙中拼搏的、與我們血脈相連的人,那些如鐵沙梨般堅韌的戰士,他們的精神從未遠去,正通過老屋、展品、口口相傳的故事,化作滋養香港的養分,讓愛國的種子在這片土地上繼續生長。這份在親情與硝煙中生長的家國魂,終將代代相傳。







 今日熱搜
今日熱搜

 本周熱搜
本周熱搜

 本月熱搜
本月熱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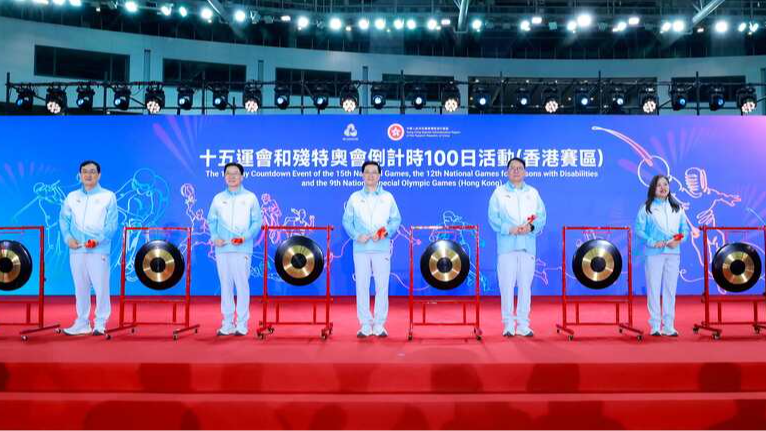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