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酸棗小孩
天下大一統,古今同此熱。雖然現代人擁有了名為“冷氣”的降溫良品,但是此物你又不能出門攜帶,吹冷氣時間太久還容易生出“冷氣病”來,不如熱點好。
古代雖然科技不發達,多少也有幾個可以抵禦炎熱的“法寶”——最常見的:竹夫人、扇子、冰塊。冰塊屬於高級避暑設備,非尋常人家所能享受的。即使如李太白、秦少遊之文人雅士有所權位者流也未必能夠或者時常享用。
秦少遊寫過一首自然主義派的《納涼》詩:“攜扙來追柳外涼,畫橋南畔倚胡牀。月明船笛參差起,風定池蓮自在香。”秦少遊是江南人,江南多水,夜幕降臨,涼風乍起,水畔柳下自然是納涼避暑的好去處。
相對於秦少遊的婉約式納涼法,李太白則是頗具魏晉風度的豪放款了:“懶搖白羽扇,裸體青林中。脫巾掛石壁,露頂灑鬆風。”
——灑脫不羈如吾故鄉人。
吾之故鄉,茫茫大平原。無水,亦無山。眼中所見,只有連綿起伏的大沙崗。大沙崗是故鄉人的避暑聖地,也是我記憶中的樂土。
無數個月明星稀、熱火繚亂的夏夜,人們在自家院子裏吃過了晚飯,丟下飯碗,甩一把汗水,抱著涼席枕頭牀單,扶老攜幼,呼朋引伴,浩浩蕩蕩向村東的大沙崗進發。
大沙崗上的沙是質地細膩的黃沙,裏面含著一些礦物質。白天的太陽光照耀下,還會金光閃閃。我曾經拿著吸鐵石去裏面找過金子,想發點意外之財,結果只吸上來一層細碎的鐵屑。
夜晚的月光下,沙崗並不會銀光閃閃,而是像水波一樣寧靜。白晝的餘溫消逝之後,人躺在沙土上就彷彿臥於清涼的水波之上。不遠處是颯颯生風的大楊樹,身邊的母親正和相好的婦人竊竊話著家常,遠處的父親正和他的死黨們邊吸煙邊說著鄉村版聊齋故事。頭頂上皓月當空。不知不覺間,你就會沉入黑而甜的夢鄉。
小時候經常在沙崗上過夜,早上被露水驚醒,一睜眼,大人們早就下地幹活去了,只剩下幾個睡懶覺的小孩子。睡眼惺忪地爬起來,抱著睡具踉踉蹌蹌地回家去。
鬧過一個笑話。有一次睡到半夜,尿急,起來小解,然後摸到涼席倒頭便睡。早上被大伯母喊醒,發現自己竟然睡在三堂哥的涼席上。“睡錯牀”這件事後來被當作典故取笑了好久。
夏日炎炎,夜間屋子裏待不住,除了颳風下雨的天氣,整個夏天的夜晚,我們幾乎都要在室外度過。大多數時候會去大沙崗上納涼,不去大沙崗的時候,就在院子裏鋪上涼席,一個挨一個地睡覺。有時候也會爬上廚房的平房頂上,鋪上涼席,一個挨一個地睡覺。沒風的時候,母親就在旁邊為我們扇扇子。
有一年夏天帶小哈回故鄉,夜裏熱,於是一大家人全都爬上房頂涼快。一字排開,躺了七八十來口人。夜空晴明,繁星密佈,一條銀河橫穿其中,看得見北斗星和牽牛織女星。這樣的情景也是許多年不曾有的。
那天晚上後半夜突然起了大風,呼裡嘩啦的,一家人全被驚醒,逃竄回屋裏了。小哈耐不住熱,哭喊著非要再回房頂上睡,於是隻好抱了厚厚的被子再次爬上房頂,在狂風呼嘯裏過了驚心動魄的一夜。
想起杜子美的那句詩來:“八月秋高風怒號,捲我屋上三重茅。”雖然不合時宜,氣勢卻是相當的。如果那夜的風再大上一二級,說不定我們也會如那屋頂上的茅草被捲上天去了。
納個涼也得具有不怕犧牲的大無畏精神。







 今日熱搜
今日熱搜

 本周熱搜
本周熱搜

 本月熱搜
本月熱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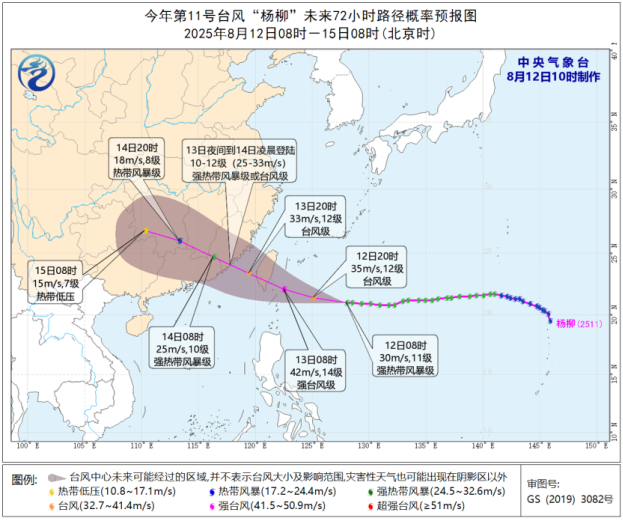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