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武昌
冬天來臨,天氣開始明顯降溫。香港的早上還是十多度,沒有北方的大雪紛飛。中午,我端着飯碗,走入廚房,找尋自己喜歡的味道。
打開抽屜,幾盒橢圓形的罐頭躍入眼簾,那是豆豉鯪魚罐頭,還有一包風味豆豉。我喜歡吃豆豉,以及用豆豉一起做的菜式,所以家裏也買了一些豆豉,以及豆豉鯪魚罐頭。
豆豉香味讓我陶醉,讓我思緒隨之飄飛。
媽媽為我做的菜式在記憶深處留存,懷念着舊時的豆豉香,悠遠又漫長,好像不曾離開,又好像不曾失去。媽媽做的豬五花腩肉蒸豆豉、南瓜炒豆豉讓我食之尋味,回味無窮。
南瓜炒豆豉,是我喜歡的菜式。將南瓜去皮去襄和種子,切成粒狀或條塊。落油爆香蒜蓉豆豉,然後落南瓜一起炒,待所有南瓜都沾上蒜蓉豆豉後,便放調味料,再加入少許水,蓋上蓋焗約3-4分鐘,一味可口的菜便做成了。
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家鄉村民基本上以種植稻穀為主,偶爾也會種植一些經濟作物,黃豆便是其中之一。
記得在家鄉村裏有一位做豆腐的鄉親也會做豆豉,黃豆是做豆豉、豆漿、豆腐的原材料。做豆豉的每一道工序都要仔細拿捏,洗、泡、煮、捂、發酵一步都不能少。那位老鄉把黃豆淘洗乾淨後,在盆裏摻入井水,將黃豆浸泡一天。傍晚,他撈起泡好的黃豆,放入大鐵鍋中煮,煙氣氤氳繚繞,他用鍋鏟舀起一顆豆子用手試了試硬度,適合後便「起鍋,濾水」。他拿起準備好的篩子,將濾過水的豆子放在篩子上鋪開晾一個晚上,風乾水分。
第二天,他拿出麵粉與菌粉攪拌均勻,倒在豆子上,用筷子攪拌,讓豆子裹上麵粉,然後拿起篩子抖掉多餘的麵粉,一顆顆豆子黏上粉團,精致又小巧玲瓏。他在提前準備的蒸籠裏放入乾淨的稻草,將黏滿粉團的黃豆倒入蒸籠中鋪展開來,蓋上一層稻草,再蓋上蒸籠蓋,放置發酵霉化七天。霉化好的豆子上面長着白灰色茸茸的毛,此時已有縷縷霉香撲面而來。把豆子挑散開,長長的絨毛便裹挾在豆子上,再倒入篩子裏晾曬一天。然後把半發酵豆子倒入洗乾淨的盆裏,再倒入白酒、鹽、切好的畺,將豆子攪拌均勻,裝入壇子裏封壇醃製一個月,便大功告成。一個月後揭開壇蓋,一陣陣濃郁豆豉香味飄逸而出。
豆豉鯪魚也是我喜歡的,逛超市時會買幾罐回家。豆豉鯪魚源於廣州,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內地開始工業化之前,許多珠三角地區的人需要到東南亞打工,因為吃不慣外國的餐飲,他們便將鯪魚炒熟,用豆豉醃製,然後隨身攜帶,這種傳統做法逐漸轉變成一種罐頭製品。到1960年左右,香港人的生活環境並不富裕,他們收入低,購買力也低,由於豆豉鯪魚罐頭價格低廉、保質期長、味道濃郁,可以單獨拌飯食用,所以也成了常見的下飯菜。
作為對過去味道的懷念,豆豉鯪魚已經成為許多香港人的集體回憶,而我對豆豉的香味情有獨鍾,時不時會用它來做不同的菜式。







 今日熱搜
今日熱搜

 本周熱搜
本周熱搜

 本月熱搜
本月熱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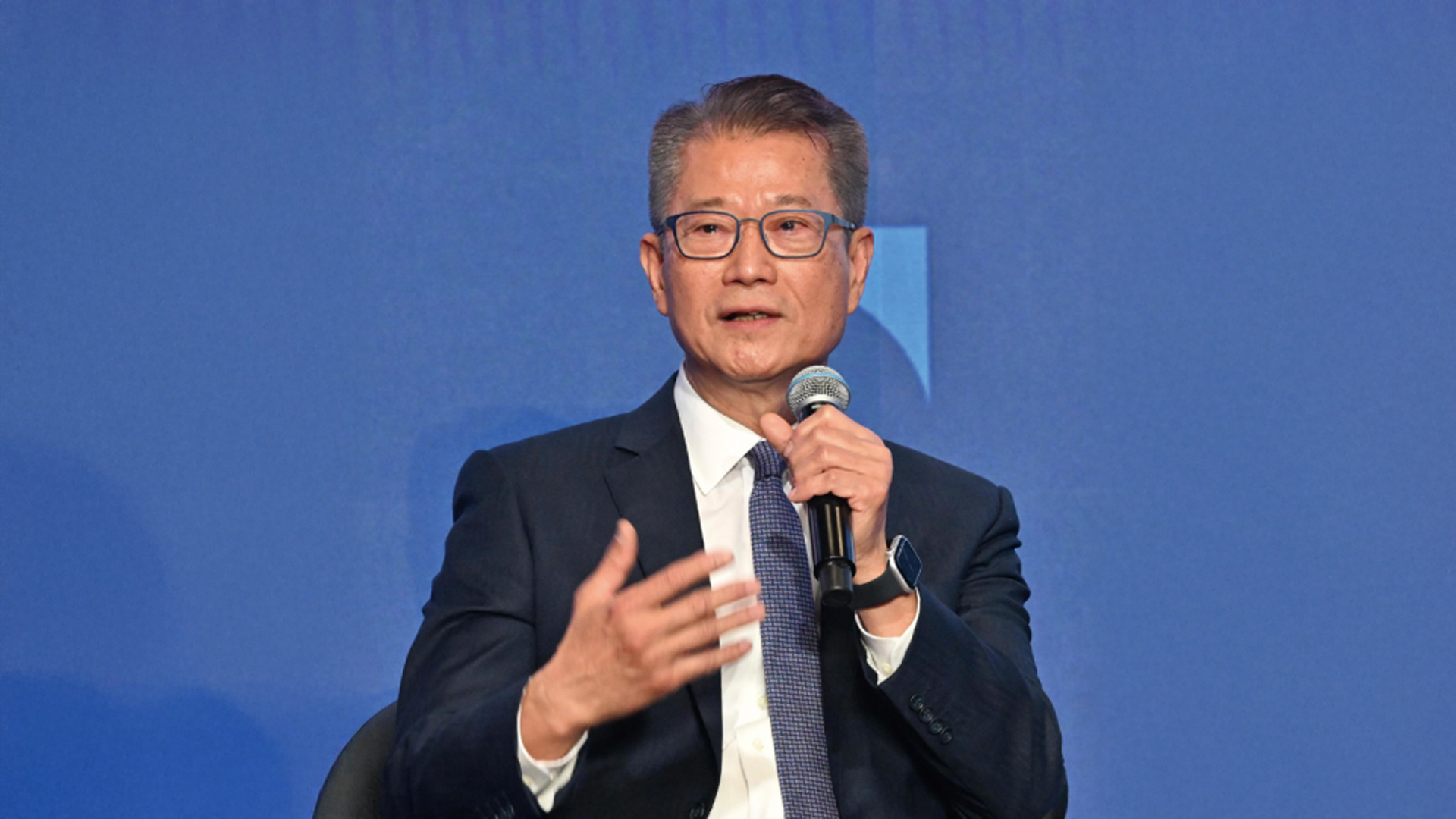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