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夢瑤
六月底的下午,在南方影業主辦的首映上,見到了《雄獅少年2》的監製張苗和導演孫海鵬。在銅鑼灣影藝戲院影廳外,邊候場邊談,人聲嘈雜,正似世間喧囂不斷,我們三個聚首潛心,又如醒獅上樁,專心只踏眼前一步。

煙火氣
寒暄之中的開場,自然聊起對香港的印象。相比於監製張苗經常到港,孫海鵬導演說,這是他第二次到香港,上次還是七八年前因工作之故,匆匆往來。“香港給我很深刻的印象是街道很窄,兩旁佈滿高樓。這些現代化的建築又不是冷冰冰的,反而是因為經歷了歲月,煙火氣很足。”孫海鵬導演邊描述的時候,邊用手比劃著,頓了頓,補充道:“還有就是路上跑的車,像巴士、小巴這些,都與其他城市不同,很有香港自己的特色。”
一個人的語言風格與專業背景是深度綁定的,本質上來說,是專業訓練塑造了認知模式、思維工具和表達習慣。學美術出身的孫海鵬導演,很習慣地就開始用畫面感描述事物,從他長期被專業“馴化”的感知與表達邏輯裡,我看到了一幅幅香港速寫。而“煙火氣”是這些速寫的核心主題,也是孫導演創作的核心主題。比如“包強”系列動畫短片,那些包子、餃子、麵條,熱氣騰騰地演繹著煙火人間的故事。比如《雄獅少年》系列,以最平凡的普通人視角,講述為夢想努力,經歷無數挫折後,依然堅守熱愛,不斷成長與奮鬥的故事。
香港印象裡,那些首先被孫導捕捉到的畫面,都是市民生活裡的片段。香港高樓繁密,一座玻璃鋼筋的森林,樓縫裏漏下的陽光被切割成碎金,強風穿過樓宇會帶著金屬摩擦的銳響,抬頭望常只見一線天光,無數玻璃幕牆彼此疊成一片晃眼的、沒有縫隙的鋼筋山巒。但是孫導都沒有描述,他低頭看向了市井,看到了日常的交通工具,看到了被人們用銳意進取的步伐,磨舊的建築。香港這座城,有許許多多人,哪怕只是走上一條天橋往下看,密密麻麻如像素點,拼出流動的光影巨畫。但也是這樣的人們,摩擦生熱出許多煙火氣息。
香港的舞獅,既是非遺項目,也是充滿煙火氣的,節日慶典、公司開業、店鋪開張都會見到,以祈求好運和驅邪。於是我問孫導,您之後的創作,會把阿娟帶來香港嗎?孫導似乎在思考,但還是點點頭:“阿娟一定還會走向其他地方的。”頓了頓,續言道:“片中有句台词:人这辈子,上山下山,就像舞狮,有自己的路要走。阿娟這個年紀還是很年輕,還是在上山,他還會去其他的遠方。”孫導表示如有機會,希望來香港取景,或者與香港合作,繼續阿娟的故事。

青春
順著年輕這個話題,聊起了這部影片的主角團和主要觀眾群體,都正在青春洋溢的年歲。我問孫導,現在的年輕人比較容易迷茫,很難像阿娟這樣堅定而純粹地追求一些目標。孫導搖搖頭,“其實並不是的,你看這兩部片子,他的目標裡都有很世俗的東西,比如第一部是為了喜歡的女孩學舞獅,為了去廣州看父母參加舞獅比賽,第二部為了在上海立足,賺錢生活。阿娟追求的夢想或者目標都沒有那麼『純粹』,但恰是這樣的,才很真實。”
孫導的回答讓我想起了錢理群教授關於年輕人如何尋路的觀點:80、90後這些人是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時代成長起來,自己的命運已有安排,順從命運聽話就能獲得想要的一切。但是現在的年輕人則不行,所以他們感到困惑。
可魯迅一百年前就說“現在的年輕人需要重新尋路”。找不到路,陷於迷茫,就吃飽喝足,睡一覺起來再想,總是可以找到一條可以邁一步開去的路。先賢有言“窮則獨善其身”,窮指無路可走。沒路走的時候,就應該照顧好自己,再徐徐圖之。比如前作《雄獅少年》,阿狗掄著兩個大鐵錘睡眼惺忪地敲打肉泥製作牛肉丸,阿娟和阿貓去找他組隊練舞獅,阿狗只問“管飯嗎”。《雄獅少年2》主角團在上海被房東掃地出門,阿娟聽到王朝雨說“包吃包住”,就開始練習拳擊,目標就是比賽獎金。
所以,路,真的是人走出來了。
先從“吃飽”開始,才有力氣、才有可能一步步走向更高遠的人生目標。
我又問,現在的年輕人吃飽可以,但不包括“苦”。如何讓年輕人像阿娟這樣吃苦耐勞呢?若您代入阿娟的角色,有沒有什麼話,想對觀影的年輕觀眾說的?
趁著孫導在思考,我補充道,香港有一座獅子山,見證香港社會發展,香港人在逆境中不屈不撓,自強不息,形成了“獅子山精神”,與雄獅少年所體現出來的精氣神很能產生共鳴。孫導點點頭:“年輕人的成長其實都會經歷差不多的東西,有類似的困惑。如果我是阿娟,我會跟香港的年輕朋友說,他們可以回家問問自己的父母,瞭解他們那一代人的故事,知道獅子山精神的具體內容,相信會對自己的成長更有幫助。”
是的,現在也可以走進電影院,看看跟他們差不多年齡的阿娟。他和同伴出身草根階層,經歷了更為艱難的生存困境。但生於野草,活成雄獅,每一個人,每一個年輕人,都應該有這種“向下的崇高”。你我應該知道,真正的英雄主義,是在俗世生活中堅守本心、奮力拼搏,做一個頂天立地又平凡生活著的普通人——內心藏有雄獅的威猛,外在生存地位縱然如野草般卑微,也能有堅韌又隨遇而安的力量。這是對樸素生命力的最高禮贊。

獅子
既然聊到了獅子,就談談《雄獅少年2》的獅子意象吧。
文學意象的產生是一個融合自然觀察、情感投射、文化積澱和藝術創造的複雜過程。但意象的起點往往是人對客觀世界的感知。人們在自然或生活中觀察到某一事物,其形態、特性與人類的情感體驗產生直觀共鳴,便可能成為意象的雛形。中國不產獅子,這來自異域的“萬獸之王”,草原生態系統的頂級掠食者,在千百年的歲月裡,逐漸融入了中華文化。
自漢朝作為貢品進入皇室,從《漢書》到《明史》,有二十多次貢獅相關的記載。獅子帶著威猛、尊貴的原始意涵,也成為皇陵的護衛者。其後,受佛教傳播的影響,獅子被認作佛菩薩的坐騎和護法者,成為人們心中祥瑞的象征,能制邪除惡,能讓人生出勇健菩提心。
舞獅,可謂古儺禮遺意,《漢書》記載漢代已有百戲藝人扮作獅子。大概是人們期望自己也能獲得獅子這樣勇猛精進的力量。至唐代,“獅子舞”更成為宮廷貴族燕樂的一部分。元稹寫哥舒翰府上設宴,“獅子搖光毛彩豎,胡騰醉舞筋骨柔。”藝人扮演獅子搖擺逗趣,遍體光彩,一旁的胡姬舞動腰肢,筋軟骨柔。
北魏《洛陽伽藍記》記載長秋寺佛像出行時,“辟邪獅子導引其前”;永寧寺拱門有四獅子,“飾以金銀,加之珠玉,莊嚴煥炳,世所未聞”。大概可以想象,各式華麗的石獅子遍佈的情景。
宋代之後,獅子逐漸走進民間。《東京夢華錄》記載重陽節以五色米粉塑成獅子,蒸熟之後放在重陽糕點上裝飾。
始建於金代的盧溝橋,佈滿了石獅子,幾百年來紋絲不動的石橋,卻無人能數清這些造型各異形態可掬的石獅子究竟有幾只,反倒生出了一句歇後語“盧溝橋的獅子——數不清”。
到了明清,福獅文化深入民間。雕獅玉如意,代表事事如意,獅馱花瓶,代表事事平安。還有獅紋長方枕、獅戲球紋朝冠耳蓋爐、三獅戲球圖柿式盒、獅戲球紋蟠龍藏草瓶,獅子就這樣從異域奇獸,走進了人們的生活日常。
所以,獅子的一聲怒吼,護的是萬千眾生,它的勇猛,並不高高在上。雄獅的形象在《雄獅少年》系列電影裡出現了兩次,一次是第一部的結尾,阿娟帶動舞獅朝着擎天柱一跃而上,化作一頭真的雄獅。另一次是《雄獅少年2》,阿娟和張瓦特對著荒地草叢苦思冥想,研究以弱勝強制敵的關鍵一招,電影的最後揭示了,雄獅一直在草叢中靜待時機,一躍而出。
雄獅的形象和舞獅的形象,都在這兩部影片中出現。它們的切換,按照獅子融入中國文化的千年歷史逆向作比擬,可以理解為一種升華。混跡世俗的舞獅,到傲立天地的雄獅。正如孫海鵬導演說:“阿娟之後可能還是很平凡,但是每個人的人生總應該有那麼幾分鐘的高光時刻。”
阿娟和舞獅是相伴出現的,而阿娟和雄獅是交替切換的。
阿娟是世俗的、平凡的,因此是真實的。沒有顯赫的地位、驚人的功業,但小人物的平凡裡藏着萬千人的樣子,他們的堅韌裡映着人性最深處的生命張力,也承載着更廣闊的社會記憶。就像舞獅在現代社會裡,更多地是穿街過巷,做各種喜慶業務,但也因此吸收了飽滿的煙火氣和人間味。孫導說:“我剛來到廣東深圳的時候,走到哪裡都看到舞獅,當時給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阿娟也是不凡的,不是每一個世俗裡掙扎的小人物都會有質變為雄獅的時刻。禁打耐摔,歷經千百般錘煉磨礪,最後堅韌不拔。對於此時的阿娟來說,“打拳可能是最公平的機會”。變強,蛻變,化為雄獅,代價就是挨打,去更殘酷的競技場上挨打,直到狹路相逢勇者勝,直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成為真正的強者,就可以化為雄獅。阿娟原本是為了掙比賽的獎金,最後也沒贏。但影片最後,他跳上擂台挑戰肖張揚,“我什么都不要,这口气一定要争回来。”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孤勇,為他正名了,這也一語雙關地回應了“打拳可能是最公平的機會”。

野草
還記得王朝雨和阿娟夜跑的對話。她讓他“說說你的願望”,他答她“賺錢唄”。她說“每個人都這麼說。說說你的故事唄。”我們都是世俗人間的凡人,大概有許多願望是雷同的,但,每一個我們,理由是不同的,志氣是不同的。王朝雨給阿娟扎好腰帶,給他鼓勵,“扎緊腰帶,為你爸媽,為大家,也為你自己。”不鬆一口氣,不後退一步,疾風知勁草。
孫海鵬導演也表示,來到南方的初印象,除了舞獅,就是這些映入眼簾的長年常青的綠意盎然。
中國文化裡,草長了數千年。一切都源於歲歲枯敗歲歲生的生命力。白居易“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直白地道出野草頑強的生命。《楚辭》寫“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離別之情如蔓延瘋長的野草,隨離人的步履越鋪越遠。秦觀寫“恨如芳草,萋萋刬盡還生”,相思之苦如生生不滅的原上草。到了近代,還有魯迅的《野草》。除此之外,還有王安石的“晴日暖風生麥氣,綠陰幽草勝花時”,愜意美好的夏日田園風光。
野草在時光裡生滅千載,疊加了中國人許多情感,提供了豐富的理解角度,加持了《雄獅少年2》裡的野草,讓它給觀眾的感覺更立體。
我問孫導,獅子和野草如此不同的意象放在一起,怎麼理解它們呢?
孫導把兩個手掌虎口相扣,說:“小草堅韌和低調,是內在的能量,獅子張揚活力,是外在的能量,對於一個人來說,這兩者就是合在一起的,才會更完整的成就一個人。”
一直在旁邊聽著我與孫海鵬導演對話的監製張苗,終於開口了,“其實這部片子的能量很『正』,它能感動像你我這樣很正能量的人。”談到“獅子”和“野草”的關係,張苗說:“我想讓觀眾理解『力量』,中國人對『力量』的理解。野草,代表平凡而無名的你我向上生長、向下紮根的力量;雄獅,代表中國文化吞吐天下,包容並取的力量。”
採訪的最後,孫導略有神秘地笑言:“片尾,一定要看完。我不善於用語言表達,但我是美術出身,我想說的話,都在鏡頭裡。一定要看完,到最後一幕。”

散場
我點點頭,在影院裡與觀眾一直坐到燈光再次亮起。伴隨著節奏振奮的片尾曲,很多影迷很有節奏地高喊“劉家娟!劉家娟!”仿佛在給擂台上的阿娟打氣,也像給自己鼓勁。曲終人散,影迷拿著票根,拿著各種周邊,對著大屏幕的巨幅海報打卡留念,意猶未盡,陸續步出影院。
王朝雨說“種子在哪裡都能夠發芽”,《雄獅少年》系列電影就像一顆種子,在影迷們心裡種下了。
那麼,換一座城,再來一個故事!
但你一定要走進電影院,看完這個故事。
(作者係香港教育大學國學中心聯席總監,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今日熱搜
今日熱搜

 本周熱搜
本周熱搜

 本月熱搜
本月熱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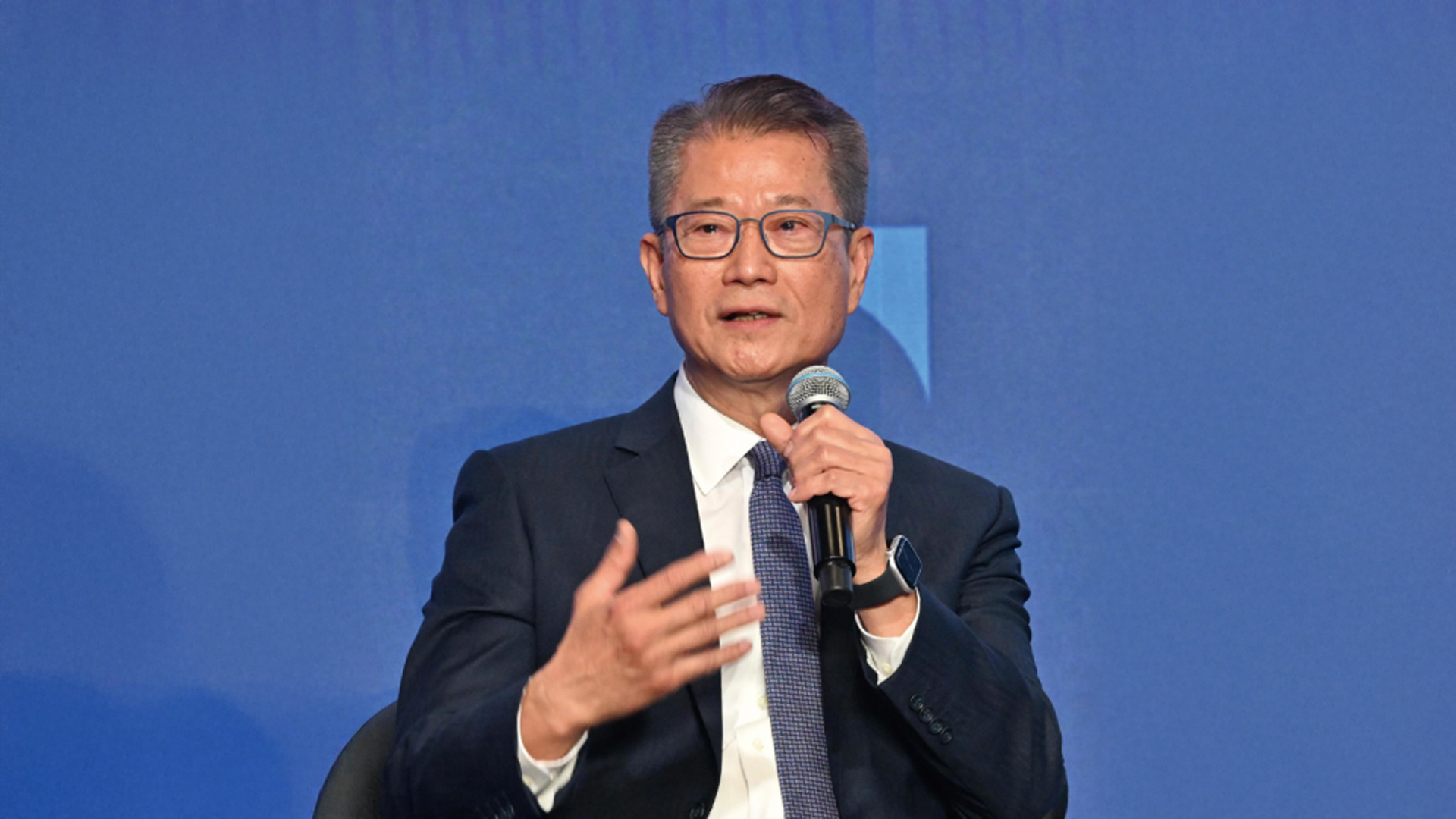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