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曦
去香港仔菜市場,看到攤位上碼放著小扎小扎的褐紅色香椿,腦海中立馬浮現出白瓷碟上躺著大大圓圓的香椿煎蛋。買了一小把,不便宜,想起魯迅先生筆下的“膠菜”與“龍舌蘭”,笑道,果然是物以稀為貴。鄉下老屋前,有兩棵香椿樹,從未覺其精貴。
中午做了香椿煎蛋,褐色的煎蛋,焦黃的邊緣,油滋滋的圓。伸出筷子撮下一塊送入口中,細嚼慢咽,滿口噙香;愜意地半瞇眼,深深深呼吸,果然是春天的味道!春天到了,味蕾的刺激最能勾聯回憶;滿目的春風揭竿而起,將記憶的城池侵略;景深之處,是白髮的奶奶提籃彎腰摘野菜,幼年的我蹦蹦跳跳追蝴蝶。
第一縷春風掠過山野的額頭,驚蟄的雷聲錘醒了酣睡的大地,細雨如牛毛針扎向泥土的深處。蚯蚓從地底伸伸懶腰,野草在地面探頭探腦,椿芽也在枝頭打著噴嚏,把自己的野心暴露。春風浩浩蕩蕩趕場子,一場又一場,春雨淅淅瀝瀝訴衷情,一遍又一遍。馬蘭頭、蒲公英、薺菜、艾蒿、鼠曲草、蕨、小筍子……趕集似的你追我趕鬧哄哄地擠滿了田坎、山坡。就連池塘邊的地皮菌也在雨水的浸潤下,以特有的手勢與季節交談。
春生萬物發,有太多的植物進入食譜中,奶奶的菜籃子豐富起來。大戶人家出生的奶奶有足夠的耐心,去野外採摘新鮮的馬蘭頭、蒲公英、薺菜,回家灼水,加上蔥薑蒜,撒上乾辣椒,熱油一激,麻油一拌,桌上就多了一道美味的涼拌菜;小筍子與蕨菜,則可以炒臘肉,出鍋添一把蒜葉,就是葷素均勻香噴噴的家常菜。鼠曲草或艾蒿,可以和糯米粉白糖做成青團,是春日餐點不可或缺的風景。地皮菌,當然是與肉泥薑絲左擁右抱,享齊人之福,開一大盆湯,蔥花這個小侍女,則翠生生地浮在上面;泥土的腥,春天的鮮,一勺熱湯從喉嚨滾下肚,腸胃舒服又熨帖。
春天的野菜是我與奶奶的饕餮盛宴,與父親無關。只要有正經的糧油米麵肉食,他的筷子絕對不會探向野菜。無論端上桌的野菜色澤多麼鮮亮,我們誘導味道多麼可口,對於父親而言,筷子一挑都是禁忌與冒犯。對於肉食的偏愛,成為父親一生的執念——吃肉就是幸福生活的標籤。父親總會及時消耗掉我們不愛吃的臘肉,並且認為香椿煎蛋完全破壞了雞蛋的味道而拒絕吃。
奶奶去世已久,父親亦不在人間,我也離開家鄉來港很多年。微信提示音響起,是鄉下堂姐拍攝老屋門前那棵椿樹圖,香椿芽在枝頭亭亭玉立,年年未變——未見你來時我本燦爛,如今你離去我依然枝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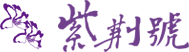





 今日熱搜
今日熱搜

 本周熱搜
本周熱搜

 本月熱搜
本月熱搜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