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台灣光復80周年。10月25日,兩岸人民將共同慶賀、共同紀念。
日本侵略中國,從台灣開始,在台灣終結。1895年,清廷在甲午戰爭中失敗,被迫割讓台灣給日本。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被殖民統治半個世紀的台灣,終於重新回到祖國懷抱。同年10月25日,中國政府在台灣省台北市莊嚴舉行中國戰區台灣省對日本受降典禮,這一天,被正式定為“台灣光復節”。

如果說全面抗戰是8年,東北抗戰是14年,那台灣的抗戰就是50年。在中華民族來之不易的勝利中,台灣民眾是抗戰的重要生力軍。同屬於中華民族的兩岸同胞,攜手並肩,共赴國難,又一同迎來了抗戰的勝利、台灣的光復。

空前恥辱,割讓一省
1895年3月24日,日本馬關,春帆樓下,清廷重臣李鴻章坐上轎子,欲回旅館。
甲午海戰失敗後,日方知道清政府急於停戰,故而在第二輪談判中提出了極為苛刻的停戰條件。李鴻章因“要挾過甚”極為憤慨,一番交涉下來,日方答應在次日揭曉真實的議和條件,這讓他心事重重。
起轎而行,還沒走幾步,一名日本暴徒突然從街道圍觀的人群中衝出來,近距離向李鴻章開槍,擊中其左臉。李鴻章滿身鮮血,當場昏倒。
隨行的醫師馬上替李鴻章進行急救,所幸子彈先擊碎眼鏡,再嵌入左眼下骨縫,並未擊中要害。李鴻章已是古稀之年,決定不取子彈,“用藥水洗治皮肉,可望補復”。
經過電視劇《走向共和》的演繹,李鴻章捱了這一槍,讓大清少賠了一億兩白銀,割地少了一處。其實,這一說法很難成立。
李鴻章馬關遇刺這天,也是日軍攻打澎湖的日子。次日,日本陸軍5000人在海軍配合下攻佔了澎湖列島,且欲直接奪取台灣,繼而在談判桌上取得更大的利益。
橫生枝節的行刺,打亂了日本軍部的節奏,他們不得不以停戰穩住李鴻章,但停戰不包括澎湖、台灣。
當時,日本國內主戰氣氛極為濃厚,“何時輕騎入燕京”是一種普遍民意。行刺李鴻章的小山豐太郎,是一名26歲的無業遊民,他的動機就是不希望中日兩國停戰。而內閣總理大臣、甲午戰爭策劃者伊藤博文的目標是,從東北和台灣開始蠶食中國。
李鴻章遇刺,引得國際輿論譁然。伊藤博文唯恐李鴻章以此為藉口回國,博取世界同情,進而推動歐美列強幹涉,乾脆直接亮出了底牌。
4月10日,談判重開。伊藤博文蠻橫地要求賠款二億兩白銀(原來是三個億),割讓遼東半島(範圍有了縮小)、台灣、澎湖,並說此次的條款“已讓至盡頭”,中國代表只需回答“允”還是“不允”。李鴻章問:“難道不準分辯?”伊藤道:“只管聲辯,但不能減少。”
拿到條款,李鴻章對日本勒索之苛、慾望之貪甚為驚愕。畢竟,台灣是大清的一個省,將一個省割讓給外國,這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
最後一輪談判中,李鴻章仍試圖與伊藤博文討價還價。中日速記員將他們的對話實錄如下:
李:賠款還請再減五千萬,台灣不能相讓。
伊:如此,當即遣兵至台灣。
李:索債太狠,雖和不誠。我說話甚直,台灣不易取,法國前次攻打,尚未得手。海浪涌大,台民強悍。
伊:我水師兵,不論何苦,皆願承受。去歲,北地奇冷,人皆以日兵不能吃苦,乃一冬以來,我兵未見吃虧,處處得手。
李:台地瘴氣甚大,從前日兵在台,傷亡甚多,台民大概是吸食鴉片煙,以避瘴氣。
伊:但看我日後據台,必禁鴉片。
談到台灣交割時,李鴻章認為一個月太倉促,要求再展限一個月,並說:“貴國何必急?台灣已是口中之物。”伊藤回答:“尚未下嚥,自感腹飢特甚。”
這次談判長達四個半小時,毫無改變,弱國無外交,果然不假。
甲午戰爭由朝鮮而起,起初並未涉及台灣,日本為何像一隻咬到獵物的狼,撕咬着台灣不放?
從大航海時代起,台灣的地位就不一般了。作為亞歐大陸板塊前沿,荷蘭把台灣當作戰略據點,使台灣成為亞洲海上的重要中繼站。
在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英法都想拿下台灣,但都鎩羽而歸。由此,清廷也認識到,台灣是一塊兵家必爭之地。1885年,台灣設置為行省,劉銘傳以福建巡撫兼首任台灣巡撫。他修鐵路,辦實業,苦心經營台灣,卻不知歐洲列強之外,日本早就對這寶島垂涎欲滴了。
德川幕府(1603—1868)末年,日本就有“北割滿洲、南收台灣,進取中國”之議;明治維新(1860—1880)之後,日本便決定執行“北進朝鮮再經滿洲入北京,南下琉球經台灣轉進南京,蠍形夾擊中國”的“蠍形政策”。
1874年5月,日本發動了明治維新後的第一次對外戰爭——出兵台灣,這是近代史上日本侵略中國的起點,清廷僅以50萬兩銀子就換取了退兵。
甲午一戰,馬關議和,清廷提出種種賠償條件,但日本仍強索台灣,就是為了取得南進擴張的基地。
《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到台灣,引起軒然大波。台灣巡撫唐景崧立即上書,表示“台灣民眾不服,其約可廢”。在京等待參加會試的台灣舉人汪春源,也會同四位台灣舉人和官員聯名上書都察院:“與其生為降虜,不如死為義民。”
從17世紀末施琅平定台灣到19世紀末,200多年間,清政府一直在不斷鼓勵大陸人往台灣墾荒定居。開發台灣的漢人,主要來自三個原鄉:福建的泉州、漳州和粵東的客家。台灣地區領導人、“台獨”分子賴清德和蔡英文的祖輩,都是清朝時從福建省漳州遷至台灣省的。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怎可拱手讓給日本?
然而,《馬關條約》終究生效了。6月2日,清廷代表李經方(李鴻章養子)到台灣辦理交接。他知道“台灣島民群情激憤”,不敢上島,於是日方派出小艦艇,把李經方接上橫濱丸號軍艦,在基隆外海上,將《交接台灣文據》交到日本代表、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的手上,完成了儀式。
這個儀式雖然空前屈辱,但其重要性在於,它是台灣主權屬於大清的證明。如果不屬於大清,何來“交割”一說?
武鬥20年,文鬥又10年
為佔領台灣,日本動用了三分之一以上、7萬多人的兵力和常備艦隊的大部分艦隻大舉南下。
在日軍登陸台灣的前5個月,由北至南的義軍反抗風起雲涌,台灣的民眾,至少死亡了5萬人,而日軍也折損不下萬人。
在台灣彰化八卦山上,有一座“乙未抗戰紀念碑”,紀念的正是《馬關條約》割台後,台灣軍民奮起抗日的歷史。
那上面有個年輕人的名字——吳彭年。1895年5月,日軍在台灣北部登陸,清廷發文命在台灣的清朝官員“內渡”。剛剛以候補縣丞來台的吳彭年抗命留下,投入駐守台灣的黑旗軍劉永福的麾下。
劉永福的黑旗軍曾經在中法戰爭中大敗法軍,是清末難得一見的善戰部隊。受劉永福之命,吳彭年率領700黑旗軍將士重創日軍,在奪回八卦山的戰鬥中,吳中彈墜馬,壯烈犧牲。
吳彭年是浙江餘姚人,出生年月已不可考,據說犧牲時年僅22歲。22歲,青春正盛,他本可安然返回大陸等待朝廷另行任用,但卻與台灣義軍生死與共。
“閩台皆桑梓之地,義與存亡。”林森是福州人,當時在台北電報局工作,也組建義軍抗日。被迫離開台灣後,他又回鄉加入了同盟會,成了國民黨元老。國民政府成立後,他當了12年政府主席,收復台灣一直是他的初心。
詩人丘逢甲,號召“舉義自守”,率鄉勇在台中、彰化一帶奮戰。義軍的武器多是長矛、鳥銃,甚至鋤頭,面對裝備精良的日軍,戰鬥慘烈而短暫。次年,隔着海峽,丘逢甲留下“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灣”的詩句。
乙未抗戰,只是台灣民眾前赴後繼抵抗侵略的起點。
1915年夏天,日本侵佔台灣20年後,台灣最大的一場武裝抗日之戰在台南噍吧哖開始。
日本人有多恨噍吧哖?他們隨便撿了一根竹竿,屠殺了當地所有高過竹竿的青年男子,甚至將地名改為“玉井”。玉井是當時東京風化區的地名,他們這樣做就是要羞辱、詛咒這個地方的女性和後代。
2014年,台南新化發現一處無名荒冢,裏面竟有白骨三千多具。經過考證,那是1915年“噍吧哖事件”時被殺害者的萬人冢,而且這只是被害者中的一部分。
最悲壯的,要數高山族民眾發起的“霧社事件”。1930年,賽德克族的族長莫那·魯道帶領六個部落的族人襲擊了日本警察學校,用弓箭、獵槍擊斃134名日本官員和家屬。
氣瘋了的日軍用飛機大炮,甚至是化學毒氣彈,鎮壓這些沒有現代武器的少數民族。起義持續兩個月,參與的部族幾乎全滅,高山部落的女人們,為了讓丈夫沒有後顧之憂,不惜集體跳崖。八十多年後,倖存者的子孫在紀錄片裡說:“對餘生而言,活着,比死去還需要勇氣。”
日本殖民台灣50年,前十年主要鎮壓漢人反抗,第二個十年主要鎮壓少數民族反抗。據不完全統計,1906年至1914年,台灣少數民族有八分之一被殺害。
1914年5月,日軍進攻太魯閣泰雅族,直接導致這個有9000多人的部落滅族。他們以為鮮血已經把台灣人嚇住了,但是,1930年的“霧社事件”,再一次展現出台灣民眾的氣節。
血腥鎮壓的同時,日本也對台灣的年輕一代進行全面日化教育。
所謂日化教育,就是“洗腦”,就是不讓保留中國籍、不讓說中國話、不讓寫中國字、不讓過中國節的文化壓制。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台灣青年,離中國越來越遠。一戰以後,以林獻堂和蔣渭水為代表,台灣本土士紳開啟了“文化抗日”。
台南連家,祖上自康熙年間入台,傳到連橫已是第七代。淪為殖民地後,連家祖宅被日本人以一塊銀元的羞辱性價格強行徵用,更屈辱的是,連橫不得不加入日本籍。
1919年,連橫寫完《台灣通史》,這是台灣的第一部通史。在這部“起自隋代,終於割讓”的鉅著中,他寫道,“‘國可滅,而史不可滅’,台灣無史,豈非台人之痛歟?台灣三百年來之史,將無以昭示後人,又豈非今日我輩之罪乎?”
蔣渭水請連橫向大眾宣講《台灣通史》,他用典雅的閩南語講,連人力車伕都會進來聽。毫無疑問,這在台灣是十分危險的。1931年,連橫修書一封,向在南京的老友張繼“託孤”:“弟僅此子,雅(連橫號雅堂)不欲其永居異域,長為化外之人。”
連震東跟着張繼到了北平、西安,認識了很多和他一樣“北漂”的台灣家庭,其中有一個稚氣可愛的小姑娘,小名英子。這個小姑娘,就是《城南舊事》的作者——林海音。她是台灣苗栗縣人,日據時生於日本,隨父母返台後,不堪忍受日本統治,舉家遷居北京。
東北淪陷後,許多台灣人和大陸同胞一樣投身抗日,甚至付出了生命,這其中就有林海音的小叔叔林炳文。林海音的父親也在接回弟弟遺骨的途中,因勞累過度去世。
1936年,連震東的妻子在西安懷孕,當他給父親報喜時,卻收到父親的遺囑:“今寇焰迫人。中日終必一戰,光復台灣即其時也。汝其勉之!”若生男孩,起名連戰,“寓有自強不息、克敵制勝之意義,又有復興故國、重整家園之光明希望”。前國民黨主席連戰的名字由此得來。
台灣史作家楊渡在總結前30年的抗爭時曾說:“武裝戰爭打了20年,文化抗日又進行了10年。武裝抗日整個過程,有人統計犧牲20萬,但我個人認為是20萬到30萬之間。”
數字之所以難以統計,是因為日方經常製造出一些冤獄。
賴清德的父親賴朝金是台北瑞芳的礦工,當年瑞芳礦工飽嘗日本殖民統治之苦,1943年日本憲警以“抗日”為名圍捕礦工,三百多人死於獄中、屍骨無存,賴朝金大概率親耳聽過同胞的哀號,親身受過殖民者的欺辱。如果他和當年同受日本人折磨的礦工,聽到賴清德之流的種種妄言,不知會作何感想。
雖然島內的起事、請願都失敗了,但也使日本當局不斷警惕:台灣民眾並未完全屈從。
“欲救台灣,必先救祖國”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了一種召喚。台灣的有志青年認識到“欲救台灣,必先救祖國”,紛紛回大陸投身抗戰。
詩人丘逢甲之子丘念台,在廣東組建東區服務隊,開展抗日活動。黃埔軍校畢業的台灣人李友邦在浙江金華組建了“台灣義勇隊”與“台灣少年團”,轉戰於浙閩一帶。曾經是童養媳的謝雪紅,在蘇聯受訓後參與成立了台灣共產黨,並潛回台灣,發動工農大眾反抗日本統治。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國民黨政府正式宣布對日作戰,《馬關條約》被廢止,台灣終於從法理上回歸了祖國。此時,台灣離開祖國的懷抱已經46年。
與對待東北不同,日本對台灣,不僅是完全統治,經濟上剝奪,還有絕對的空間與足夠的時間,能在文化、教育、宗教乃至意識層面,進行同化。
從日本對台灣的統治方式即可看出其用心。日本先以軍事,鎮壓台灣民眾的反抗;繼以殖民統治,磨滅台灣民眾對中國的眷戀與關係;進而提出“內地延長主義”,灌輸台灣是日本本土的延長的觀念;最後以“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為名,將台灣的資源與日本本土做完全的結合。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日本則用最黑暗的“皇民化”運動,來消磨台灣同胞的中國心。報紙上的中文欄目全部消失了,中國姓氏被要求改為日本姓氏,祖宗牌位被封禁,代之以日式神社。
“皇民化”雷厲風行的時候,日本警察一看到台灣民眾穿着布扣子做的台灣服,就會當場用剪刀剪去布扣子。日本人說:“台灣服是支那服,台灣民眾認為支那是他的祖國,所以一定要廢止台灣服。”所有反抗都被壓制着,連用收音機聽大陸的廣播都可以入罪坐牢,台中央書局的莊垂勝就因此坐了一年牢。
面對家鄉親友回家的呼喚,悲痛的林海音毅然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我們現在是失去了故鄉,但是回到故鄉,我們便失去了祖國,想來想去,還是寧可失去故鄉,讓可愛的故鄉埋在我的心底,卻不要做一個無國籍的孩子。”
在台灣,那些自願改姓日本姓氏的人家,統治當局提升他們為“皇民”,可以享受種種特權。比如,戰時實行配給制,台灣同胞能獲得的配糧,只是在台日本人的一半,“皇民”可以得到介於日本人和台灣人之間的數量。
即便是為了餬口,願意成為“皇民”的也不多。在日本侵華戰爭開始時,“皇民”佔全台人口不過4%。太平洋戰爭開始,“皇民”運動加速進行,增加到7%左右。大戰結束時,“皇民”人數佔10%左右。
那些自願成為“皇民”的台灣民眾,往往比真正的日本人還要“日本人”。
鼓吹“台獨”的前台灣地區領導人李登輝家境不差,小時候還在私塾學習“漢文化”,但老師其實是隻是以日文來誦讀《論語》跟《孟子》等《四書》。1940年,讀中學四年級的李登輝改名“巖裡政男”。李登輝曾說,改姓“裡”留下了“李”這個音,很多姓“李”的都改成“巖裡”“小裡”“北里”等等;“巖”是因為李家來自福建龍巖。
“皇民化”運動有個重要目的,就是在台灣徵兵,為“南進”侵略政策充當炮灰。二戰爆發後,日本從台灣強徵近30萬青壯年,這其中有3萬人確定死亡、10萬人受傷。
隨着太平洋戰爭爆發,大批台灣青年被徵召去南洋,有去無回。李登輝的哥哥李登欽就加入了日本海軍,命喪東南亞。1944年,李登輝被編入日本千葉市千葉高射炮部隊做見習士官,未及參戰,就在千葉迎接了日本的戰敗。在日本帝國大學和日軍中受的教育,使得他在人格底色上就扭曲了。
如果讓台灣兵開赴大陸戰場,往往遭到直接對抗。1939年10月10日,基隆壯丁300人被徵入伍,在領得槍械後,立即“譁變”,消滅日寇30名,在隨後的激戰中又消滅日寇145名,然後持械退入山中開展游擊戰。
時代的一粒灰,落到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在歷史學家楊渡三個叔公的命運中,也可見一斑:
楊渡的三叔公,被迫在上海幫日本人當翻譯,抗戰勝利後,被當成日本人、漢奸,幾乎死於上海,戰後死裏逃生回到台灣;六叔公被日軍徵召,遠赴南洋當軍夫,差點餓死於南太平洋的荒島上,最後是靠着美軍帶回家;而留在家鄉的二叔公,左腿毀於1944年美軍對台北的大轟炸。一個小小家族,在一場戰爭中,竟有如此不同的際遇,這或許就是台灣民眾命運的縮影吧。







 今日熱搜
今日熱搜

 本週熱搜
本週熱搜

 本月熱搜
本月熱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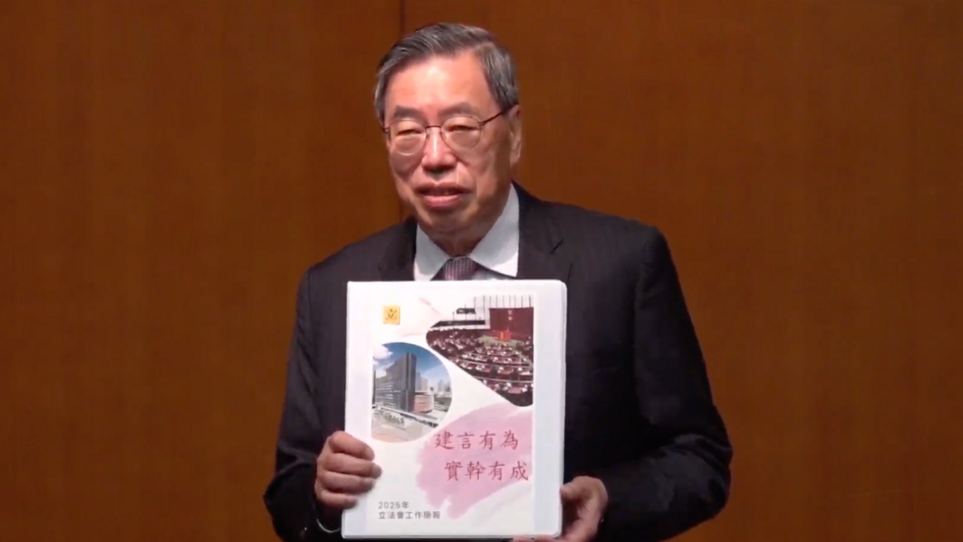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