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鄧思穎 |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首先論述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與香港的中國語文教學的關係,提出以通用為綱,以差異為目。通過將詞彙學習作為本文的討論重點,建議詞彙可劃分為文言詞、方言詞、社區詞、普通話詞;以學習普通話詞為核心,適當把文言詞納入教學當中,並系統比對方言詞、社區詞跟普通話詞的異同。通過學習語言,進一步了解文化,以語言作為文化的傳播載體,並以語言作為文化研究的對象,加深對文化的認識。學習的大方向,是以文化為本,以形式為末。通過語文學習,增進學習者的文化認同,建設現代文明。秉綱而目張,執本而末從,期望語文教學的問題能迎刃而解。
國家通用語言文字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九條早於1982年寫明「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推廣國家通用語言,可謂憲法規定的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以下簡稱「《語言文字法》」)於2000年10月31日獲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並在2001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該法的制定,彰顯了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重要性,同時也是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法制保障。
《語言文字法》第一條明確說明,「為推動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規範化、標準化及其健康發展,使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在社會生活中更好地發揮作用,促進各民族、各地區經濟文化交流,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這是我國以法律形式確定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地位的表現。語言文字的「規範化」「標準化」「健康發展」這幾個關鍵詞,可謂該法的精髓。《語言文字法》的制定,讓語言文字的使用有了明確的方向,並有可依照準繩,無論對語言文字的研究亦或是應用等方面都非常重要。

至於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定義及範圍,《語言文字法》第二條作了清楚的界定:「本法所稱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是普通話和規範漢字。」在第三條中,有關語言文字的工作也有清晰的說明:「國家推廣普通話,推行規範漢字。」由此可見,這兩條確定了普通話和規範漢字作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法律地位。為了行文方便,在不涉及文字討論的語境裡,本文也會採用「國家通用語言」一語。
至於「普通話」的定義,非常清晰。國務院在1956年2月6日所發布的《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中有說明,普通話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
至於「規範漢字」,即是以《通用規範漢字表》為準。該字表由教育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研製,整合了1955年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1964/1986年的《簡化字總表》、1988年的《現代漢語常用字表》、1988年的《現代漢語通用字表》等文獻,於2013年正式頒布。簡而言之,規範漢字就是經過整理規範後的簡化字。
順帶一提,按照教育部在2009年7月21日公布的英文新聞公報,「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英語翻譯為「the Standard Spoken and Written Chinese Language」。根據這個翻譯,「通用」一詞的理解,可以對應英語的「standard」。至於「普通話」,則用漢語拼音的拼寫「Putonghua」用於英語的語境,並用英語作說明:「a common speech with pronunciation based on the Beijing dialect」。此外,教育部的英文新聞公報偶爾採用「Mandarin」「standard Mandarin」等來對應「普通話」。國務院的英文網頁中,用「Mandarin」的場合比用「Putonghua」的場合多得多。至於香港地區的情況,在英語語境中把「普通話」一詞翻譯為「Putonghua」或「Mandarin」都有,但前者較為常見,往往用於香港特區政府的文件和公函。比如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在中小學普通話科的英文文件中,就是使用「Putonghua」一詞。2020年印發的《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全面加強新時代語言文字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將「以推廣普及和規範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為重點」作為指導思想之一,「語言文字規範化、標準化、信息化水準進一步提高」等作為主要目標。這裡所說的「規範化、標準化」,與《語言文字法》的精神可謂一脈相承。至於「信息化」一點,更好突顯了新時代語言文字工作的新任務,以適應時代的急速變遷。《意見》中與香港相關的部分,主要有兩點:第十二點談及「提高服務國家戰略的能力」,提出「加強粵港澳大灣區、自由貿易試驗區、『一帶一路』建設等方面的語言服務」,包括開展語言專項調查、開展語言生活狀況監測、加強國家應急語言服務等方面;第十五點談及「深化與港澳台地區語言文化交流合作」,提出「支持和服務港澳地區開展普通話教育,合作開展普通話水平測試,提高港澳地區普通話應用水平。加大與港澳台地區青少年語言文化交流力度,組織開展中華經典誦讀展演、語言文化研修等活動。加強與港澳台地區在科技術語、中文信息技術、語言文字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綜合上述這兩點,與香港相關的語言文字工作,主要涉及加強語言服務,善用研究和應用成果,提供符合社會需要的服務,更好地滿足社會語言需求。加強內地和香港交流合作,包括普通話教育、普通話測試、文化活動、學術研究、人才培養等方面。
回歸后香港中國語文教學的發展
自回歸祖國以來,香港語文教育的主要工作對象,可用四個字概括:「兩文三語」,即重視「兩文」的中文、英文,還有「三語」的普通話、粵語、英語。以中國語文教育為例,正如課程發展議會在2017年編訂的《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中所指出,「提高運用語言的能力,掌握規範的書面語,能說流利的粵語和能以普通話溝通」就是主要任務之一。中國語文教學的基本理念,就是要「培養善用『兩文三語』溝通的人才,以提高香港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同時促進香港與內地的交流和聯繫。『文』指書面語,『語』指口語」。除了兼顧包括白話文和文言文的「書面語」和普通話和粵語的「口語」外,該指引頁特別重視「運用規範書面語的能力,以避免學生的表達受口語或網絡語言影響」。除了中國語文科以外,自1998年以來,普通話科被正式納入香港小學至初中的核心科目,目的是確保所有中小學生都能夠學好普通話。至於普通話科的課程理念,課程發展議會在2017年編訂的《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普通話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中明確指出,「香港屬於粵方言區,粵方言和普通話在語音、詞彙、語法上有同有異,本港普通話科的學與教,應以廣東人學習普通話的難點作為重點,以提高學與教效果」。
特區政府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在2024年11月6日回覆立法會議員提問時所作的書面答覆中,清楚闡釋「教育局一直積極推動普通話教學,並採取多元策略,從課程、學與教支援、學生活動、教師專業發展等各方面,推動學生在課堂內外學好普通話」。《行政長官2024年施政報告》提出,「撥款約4.7億元強化英語、普通話和其他語言的學與教」。蔡若蓮在上述書面答覆中,更具體說明「教育局在語文基金預留約兩億元,於2024/25學年向每所公營中小學發放一筆過津貼,以營造豐富的普通話語言環境,加強普通話學習氛圍」。由此可見,特區政府在推動普通話教學、提升普通話水平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綜上所述,香港的中國語文教學主要以「兩文三語」中的「一文兩語」作為教學宗旨。「文」方面,重點在於「規範的書面語」;「語」方面,就是訓練普通話和粵語的溝通能力。教學的目標,離不開兩大方向:掌握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辨認地區差異。 換句話說,「文」就是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語」應平衡普通話和粵語,提升學生口語能力,加強學生對相關口語的語言知識。
語言是一個包含語音、音韻、詞彙、語法、語義的系統;簡單來說,就是一個擁有「形音義」的系統。無論是語文學習還是語言使用,都不能把這個系統割裂。以普通話為例,普通話就是一個包含「形音義」的完整系統。「音」,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所謂「形義」的詞彙語法等,就是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只有把「形音義」結合起來,才是完整的普通話。「規範的書面語」教學,不能只管詞彙語法;普通話的教學,也不能只抓發音。目前香港語言教育的現狀,往往存在「白話文與文言文混用現象」「用粵方言讀出中文書面材料的現象」。 這些情況,肯定是不適合的。
我們要充分意識到語言是一個系統,一個整體。「文」和「語」的教學和使用,應該要一致,不能割裂。理想中的中國語文教學,應該要把「文」和「語」結合起來。換句話說,就是以掌握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為綱,用一個統一的系統講授語言的形音義,那就是結合北京音、北方話、典範的現代白話文的普通話;以辨認差異為目,通過對粵語、普通話的對比,了解兩者的異同,加深認識。把兩套不同的形音義系統區分開來,不能相混,從而做到秉綱而目張,學好語文,提升水平。
建議在教學中將詞彙分為四大類
詞彙作為組成語言的一個重要的部分,在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工作中,尤其是香港的中國語文教學中,尤為重要。沒有科學的分類,往往難以掌握好國家通用語言的詞彙,也難以辨認出語言的地區差異。本文建議詞彙可劃分為以下幾大類:文言詞、方言詞、社區詞、普通話詞。
文言詞,又稱「古語詞」,即「書面保存下來的古代詞,有文言色彩」,基本以先秦漢語為基礎。國家通用語言即普通話,則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作為基礎和規範。因此,我們應充分認識到文言文與白話文有別,文言文與國家通用語言有別。文言文的詞彙語法,不能全盤用於國家通用語言。例如,古漢語第一人稱的「吾」「余」等,還有第二人稱的「汝」「爾」等代詞,雖然《現代漢語詞典(第七版)》收錄了,但明確標注為書面上的文言詞語。《荀子.勸學》中有一句:「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當中的「水」,用作動詞,這是古漢語的用法。上述的代詞,還有用作動詞的「水」,顯然並非普通話詞語,不屬於國家通用語言。然而,不少文言詞仍然活用於當代語言裡,如形容說話的「侃侃」、表示獨一無二的「絕倫」、形容山高的「崴嵬」等,都屬於文言詞,用在一定的場合,往往能產生莊重典雅之效,既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又能豐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
方言詞,在香港專指粵語詞。香港的方言詞,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有普通話的對譯,可稱為「可譯方言詞」,如名詞「褸」(大衣)、動詞「喊」(哭)、形容詞「牙煙」(危險)、代詞「佢」(他)、副詞「正話」(剛剛)、句末助詞「喇」(了)、「嗬」(吧,對嗎)等。這些方言詞,可以全轉為普通話,用普通話已有的詞彙來表達。關注可譯方言詞在普通話中的表達,可作為學習「粵普對應」的重要部分,力求避免把這一類方言詞帶入普通話裡。
另一類方言詞則不太容易找到普通話中的直接對譯,可稱為「特有方言詞」,例如「腸粉」「燒味」「粉果」「魚蛋」等生活詞彙,尤其是飲食方面,很具地方特色。事實上,不少生活上的特有方言詞,已被收錄在《現代漢語詞典(第七版)》中,如「河粉」「蛋撻」「埋單」等。這些特有方言詞,反映了地域文化的特色,往往不能也不必翻譯為普通話。在中國語文教學方面,特有方言詞值得保留。通過特有方言詞的教學,既可以讓香港學生了解地域文化,認識多姿多彩的中華文化,又可以增強學習動機,提高投入感。
此外,香港不少地名也保留了方言詞。這些方言詞的普通話發音值得好好整理,並向學生有系統地介紹,幫助其掌握正確的普通話發音,準確用普通話表達身邊熟悉的生活環境,例如「禾輋」的「輋」(shē)、「鰂魚涌」的「鰂」(zé)和「涌」(chōng)、「深水埗」的「埗」(bù)、「大埔滘」的「滘」(jiào)、「黃埔」「大埔」的「pǔ」和「bù」兩種不同讀法等。這些方言詞的學習,不僅是普通話發音的問題,也可以從中了解地域的地理特點,加強學生對香港以及華南地區的認識。
社區詞的產生,則是「由於社會制度的不同,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體制的不同,以及不同社區人們使用語言的心理差異」。 有些社區詞,「直接因政治、經濟、文化、心理等因素的不同而產生」,可稱為「核心社區詞」;有些則「跟政治、經濟、文化、心理等因素只有間接的關係,甚至沒有什麼關係,純粹因地域差異而有區別」,可稱為「邊緣社區詞」。「核心社區詞」的例子,如「安老院」「八達通」「回鄉證」「居屋」「專線小巴」等常見的生活用語,流通於香港社會,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過,一旦離開香港,在內地和其他華人地區,這些詞就不使用了。
至於「邊緣社區詞」,往往跟社會制度的差異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以香港社會表示清點計算的「點算」為例, 那是香港社會繼承了晚清民初的書面語,在香港的中文中保留下來的用法。嚴格來講,既非文言詞,又非方言詞,但目前還沒被普通話所接受。這種邊緣社區詞,值得廣泛調查,並在中國語文教學中多加說明,讓學生了解其獨特性。如若放眼全球華人所使用的漢語,就會發現不少詞彙的差異,這些差異同時也正好反映了地域上的差異。例如,中國內地所說的「出租車」,在不同的華人地區,會說成「計程車」「的士」「德士」。即使內地用「出租車」一詞,加上動詞「打」,還是普遍接受「打的」的說法,當中的「的」,就是「的士」。事實上,「打的」這個詞,已被《現代漢語詞典(第七版)》所收錄,作為普通話的口語詞。又如「自行車」「自由車」「腳踏車」「單車」「腳車」等,流通於不同的華人地區。又比如,「窩心」一詞在不同的地區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一种表示貶義的噁心,另一种則表示褒義的溫暖。又如英語的「digital」,可以翻譯作「數字」「數碼」「數位」,也有著地域間的差異。通過了解全球華人用語(包括社區詞)的異同,建構能通用於全球華人的共同語,這就是所謂「大華語」的構思。
普通話詞以北方話為基礎、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規範的詞彙,也就是《現代漢語詞典》等權威工具書中所收錄的詞彙,有一定的規範性。將其作為標準,組成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核心部分。普通話詞在不同的語境裡,往往有不同的叫法,如「規範書面語」「標準中文」 「通用中文」等。
普通話詞每年都會匯入新詞語。例如,中國國家語言資源監測與研究中心、商務印書館等,每年都會公布口語、網絡普遍接受的「漢語盤點」。以「漢語盤點2023」為例,「十大新詞語」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全球文明倡議」「村超」「新質生產力」「全國生態日」「消費提振年」「特種兵式旅游」「顯眼包」「百模大戰」「墨子巡天」,而「十大網絡用語」包括「愛達未來」「煙火氣」「數智生活」「村BA」「特種兵式旅游」「顯眼包」「主打一個XX」「多巴胺穿搭」「命運的齒輪開始轉動」「新職人」。這些新詞既反映了語言的生命力,又能讓人們從中了解當代社會的最新發展。從規範化的角度來思考,加大廣播影視、網絡資訊等相關領域的「監督檢查」,加強「監測研究和規範引導」,強化「規範和管理」是有必要的,務求做到新詞的「規範」「標準」「健康發展」;從語文教學的角度來看,尤其是香港的中國語文科和普通話科,雖然課程發展議會於《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中曾指出「避免學生的表達受口語或網絡語言影響」,但從普通話口語把新詞適當引進到教學裡看來,既可提升學習趣味,又可以讓香港學生了解內地在新時代的新動態、新發展,吸收新資訊。如此,香港學生到內地學習旅遊,遇到新詞新事物,就不會覺得陌生。
綜上所述,詞彙學習可劃分為文言詞、方言詞、社區詞、普通話詞學習。通過對文言詞的學習,注意文言和白話之別,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寫作中更顯莊重典雅。通過辨認方言詞,一方面作好粵語與普通話的對比(尤其是可譯方言詞),避免「方言入文」,另一方面通過特有方言詞,了解地域文化特色,領略中華文化的豐富性。通過認識香港乃至全球華人的社區詞,無論是核心社區詞還是邊緣社區詞,可開拓學生視野,使其視野更開闊。
普通話詞的學習是中國語文科和普通話科的基礎,為掌握好現代漢語奠定扎實的根基,也是認識當代中國的重要工具。語文學習以通用為綱,加強普通話詞的學習,並適當把文言詞納入教學當中,提升語文修養;以差異為目,系統了解方言詞、社區詞跟普通話詞的異同,務求做到秉綱而目張。
語言作為文化傳播載體
通過語言了解文化,由此把語言和文化聯繫在一起,建立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這種關係建基於兩種情況:以語言作為文化傳播載體,以語言作為文化研究對象。
以語言作為學習文化的工具,一直以來都是基礎教育所重視的一環。正如課程發展議會於《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普通話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中所指出,香港的中國語文科,學習任務主要是要讓學生「感受語言文字之美,培養語文學習的興趣」,「透過文學的學習,可以引導學生感受語言文字和思想內容之美,培養善感的心靈,陶冶性情,發展個性,美化人格,促進全人發展」「鼓勵學生熟讀或背誦若干蘊含豐富文學、文化內涵的經典名篇,以積澱語感,提高語文素養」。無論研讀現代篇章還是古代作品,都以語言作為形式。通過語言這個工具,欣賞文學,增進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
至於後者,即以語言作為文化研究的對象,屬於以語言學的視角去考察語言,從而了解文化。所謂語言學的視角,我們可以通過語音、音韻、詞彙、語法等形式,觀察語言有趣的一面,加深對其背後文化的認識和認同。以詞彙教學為例,從詞彙的多樣性,認識祖國的南北古今。例如,通過粵語方言詞「頸」(脖子),我們可以認識古漢語的「頸」,學會《莊子.馬蹄》「喜則交頸相靡」中「頸」的意思。再延伸到普通話的「脖子」,通過詞彙的變化,還有加上「子」尾的要求,一併解說為什麼普通話要加「子」尾,並由此產生出一系列加上「子」尾的名詞,如「桌子」「椅子」「刀子」等。漢語名詞從古到今,經歷過從單音節到雙音節的歷時發展過程。以宏觀的視野,體會語言的變與不變,從而加深我們對漢語及中華文化的認識,達到觸類旁通、一葉知秋的效果。
又如「漢語盤點 2023」所選出來作為「十大網絡用語」之一的「愛達未來」,原本來自2023年在杭州舉辦的亞運會的大會口號:「心心相融,@未來」,當中的「@」,讀作「愛達」,即英語的「at」。為甚麼「at」讀作「愛達」呢?從語言學的角度,這個問題就很好說了。英語「at」的韻尾是個塞音「t」,但普通話音節結構中卻不允許塞音做韻尾。因此,只能把「at」這個音節拆開為兩個音節來讀,即用「愛」來讀「a」,用「達」來讀「t」。這樣拆開後,「愛達」表述更有意義,借此共迎美好的期許,寄託著面向未來,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良好願望。 這樣充滿創意的語言事實,既突顯漢語和英語音韻的差異,又可描繪出祖國在新時代的發展,讓語文學習更具生動趣味。
從語言認識文化,學習的大方向,應以文化為本,以形式為末。香港的中國語文教學,重視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共通特點,彰顯古今乃至地域差異所呈現出的多姿多彩的中華文化,進而鼓勵年輕人積極投入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新發展中去。只有語言相通,才能心靈相通。全面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期望「以語言相通促進心靈相通、命運相通」。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上強調,加大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推廣力度,促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樹立命運相通的共同體理念,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國家發展的大方向。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工作,在新時代有重要的使命,並非為做而做,而是為了實現偉大的理想而進發。通過語文學習,增進文化認同,建設現代文明,可謂任重道遠。只要明白這一點,就知道什麼是語文學習的綱目本末:以通用為綱,以差異為目。以文化為本,以形式為末。秉綱而目張,執本而末從。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4年10-12月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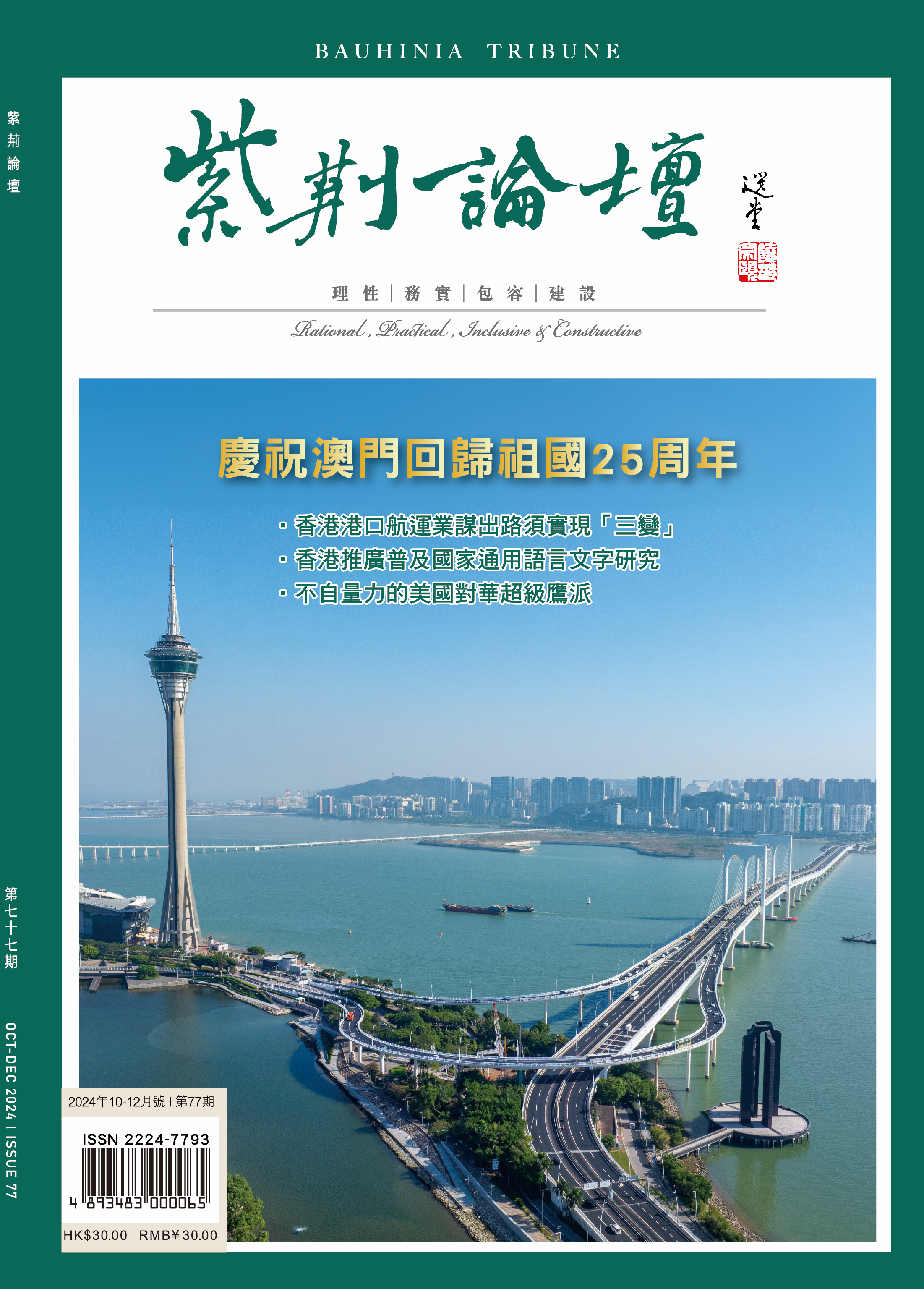







 今日熱搜
今日熱搜

 本週熱搜
本週熱搜

 本月熱搜
本月熱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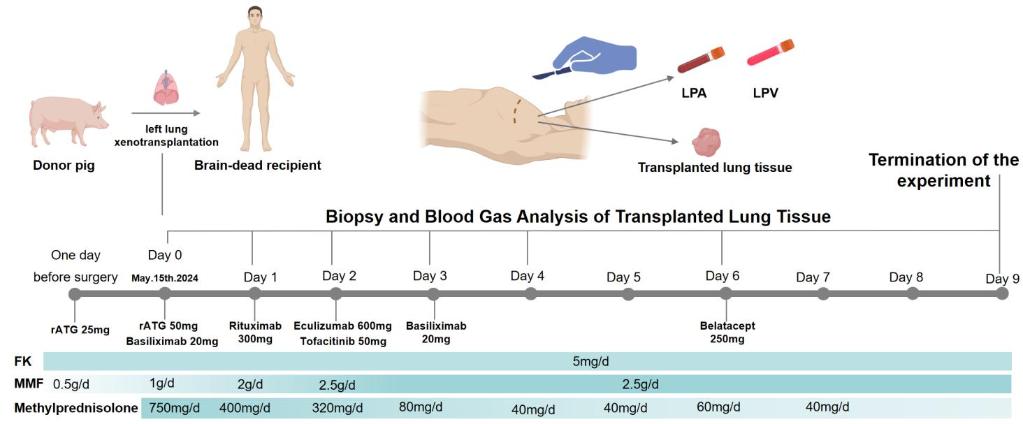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