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期間,一條短視頻被網民頻頻轉發:夜幕降臨,一座古老的村莊流光溢彩。沿着波光粼粼的水塘,數十米長的餐桌一字排開,景泰藍銅爐熱氣氤氳。這場大型火鍋宴開席的同時,池塘中央的平台上演青春民謠,天空中煙花絢麗綻放……
這是位於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區興橋鎮的釣源古村。這座擁有上千年曆史的古村始建於唐末,是北宋著名文學家、政治家歐陽修的後裔和同宗聚集地,曾走出過9位進士、32位舉人,被譽為一部濃縮的古廬陵文化史。
僅僅幾年前,釣源還深陷困境——由於人口流失、房屋破敗,這座千年古村幾乎瀕臨消失。如今,它是不少旅遊博主口中“驚豔的寶藏古村落”,被國內多個高端論壇、大型活動選為舉辦地。古村振興的“煥新方法論”,也被收錄進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哈佛大學等機構的案例庫。
追溯釣源蝶變的故事,需要把視線拉長至20多年前。它經歷了中國鄉村在城鎮化浪潮下最具典型性的“空心化”危機,遭遇了古村保護常見的波折:單純依靠政府財政撥款的“輸血式”維護難以為繼、“凍結式”保護未能挽救人去樓空的衰敗、不成功的商業開發在短暫熱鬧後留下“一地雞毛”……
雖然政府的保護力度逐年加大,但我國每年仍有不少自然村在消失,其中不乏具有重要文化價值的古村落。釣源是如何擺脫困境的?它的失落、迷茫與重生能給大量亟待保護的古村落帶來哪些啟示?
20多年曆經風雨沉浮
吉安古稱廬陵,釣源古村因歷史上交通便利、物阜民豐,鼎盛時期被稱為廬陵“小南京”。從高處俯瞰,古村規劃根據地勢高低順勢而為,以八卦布局,疏密有致、移步換景。村內有150棟明清贛派建築,道路整潔、流水清澈,青磚黛瓦被2.6萬餘棵古樟樹環繞。
“以前村裡的垃圾隨便亂扔,有的就丟在池塘邊,水也被污染了。路都是泥巴路,房子都是瓦房,很多人搬入新房子後,有些老房子就糟蹋嘍。”歐陽文忠祖祖輩輩都生長在釣源古村,對村裡的變化十分感慨,“現在老房子全都修繕過,路平平整整,池塘裡的水清得見底,還有魚嘞!”

古村一度人煙稀少,如今人氣旺盛、生意興隆。歐陽翠霞今年24歲,從小就在村裡長大,她說:“古村開發改造後小店多起來,工作崗位增加了,我現在已經是釣源古村餐飲部的領班了。在村裡就能就業,不用外出打工,換作以前想都不敢想。”
目前,釣源有茶館、咖啡店、香堂等50餘種業態,150多套民宿能夠容納300人。2024年遊客量59.14萬人次,營收1800萬元。吉州區文廣旅局副局長袁玉琼說,今年一季度,古村景區主營業務收入722萬元,同比增長41.2%。
釣源的保護之路是一條跌宕起伏的曲線——
早在20多年前,當地政府就已開始進行古村保護,嚴格控制建設,村內沒有新建一處民房,村落形態由此得以完整保存。2010年獲評中國歷史文化名村,2012年被列入第一批中國傳統村落,2015年獲評國家4A級景區……
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大量年輕人外出打工謀生,村民陸續遷出。至2019年,釣源僅剩20余間房屋有人居住,且多為留守老人。古建築被用作農具倉庫,牆體開裂、屋頂漏雨。在此情形下,釣源屢屢被警告撤銷4A級景區資質。
興橋鎮便民服務中心主任劉芳說:“那幾年每到颳風下雨,房子漏水的情況經常發生,甚至出現倒塌。村民給我打電話說‘政府要管吶’,要求給他們修繕。但因為很多房屋不是文物,沒有專用資金,我們很着急但也很無奈。”
吉州區委書記尹冬苟回憶,2020年他勘查村口的祠堂,發現這座原本高大精美的建築已成危房,瀕臨倒塌,不時有瓦片、木頭從屋頂掉落。他拄着木棍小心翼翼進入院中,滿目雜草叢生、垃圾遍地,心情十分沉重。
與多數傳統村落一樣,為避免大規模拆舊建新造成破壞,釣源當年採取的是“凍結式”保護模式,維護資金單純依靠政府撥款。雖然每年投入數百萬元,但陷入老房子“修了倒、倒了修”的低效循環。
與此同時,隨着年輕人不斷外出打工謀生,村莊日益“空心化”,傳統技藝、民俗活動等非物質文化遺產瀕臨失傳,古村逐漸失去了記憶與活力。
圍繞難點、痛點開展修復與改造
新的轉折發生在2021年。吉州區政府與有古村修繕保護開發利用經驗的十里芳菲文旅集團開展合作,探索出一條“政府主導+市場運作+村民參與”的保護與開發之路。
經過短短几年,釣源煥新重生。改造工程的成功,關鍵是圍繞古村落保護普遍存在的難點、痛點展開:
——避免“千村一面”,注重保持古建築和鄉村風貌鮮明特色。
十里芳菲團隊秉持對古建築“修舊如故”“最小幹預”原則,精細修復。工程人員使用傳統青磚、草木灰填縫工藝,手工清理廢墟里的原有建築材料,最大限度保留建築原始風貌。比如,在修復已經坍塌的綸祖祠過程中,揀出老磚重新砌築,還原其古樸風貌。

——彌補城鄉發展差距,集中治理鄉村環境雜亂差。
城裡人去鄉村旅遊,吐槽最多的是垃圾、廁所、蚊蟲以及住宿不舒適等問題。通過系統、科學地建設改造,當下的釣源成為沒有蚊蟲、生態優美的現代化村莊。
2萬多棵樟樹形成驅蚊避蟲的天然屏障;通過暴曬殺菌、水生動植物培育修復水生態,構建“海綿水系”實現雨水自循環;改造村內的“七星伴月”水系統,種植水草近800平方米;與泰國專家合作改良土壤,推廣自然農法,建立稻魚鴨共生系統,實現“零化學幹預”的有機種植……
此外,老房子改建的民宿內部植入地暖、智能家居等現代設施,為遊客打造“房屋外觀越千年,內部功能超五星”的居住體驗。

——打破村民對古村保護冷眼旁觀甚至牴觸的心態,促使他們成為受益者、參與者。
釣源村村民易愛華說:“以前村裡搞旅遊,政府每年給400塊錢,有遊客參觀就要我們開一下門。我有點不願意,因為我們還要忙着種田、收地。”
2021年,當地政府將全村150棟古宅集中收儲,進行租賃流轉,通過“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帶動村民增加收入。成立村企合作社,讓村民通過租金、股金、薪金“三金”共享發展紅利。古宅村民由此戶均年增收4萬元,村集體經濟年增加30萬元以上。
另外,創造就業、創業空間,目前有80餘名村民在景區就業,返鄉青年創辦非遺工坊、民宿,形成“家門口經濟圈”。如今的釣源遊客不斷,節假日民宿一房難求。
——打破對政府“輸血”依賴,通過市場打造鄉村自我“造血”能力。
經過對產業鏈的培育,帶動周邊農副產品銷售超2000萬元,彩稻餈粑、冬酒等成為爆款旅遊商品。村裡還布局了櫻花長廊、四季花境等32個打卡點;落地陶藝工坊、香樟精油作坊等50餘個業態,形成“吃住行遊購娛”全鏈條服務;舉辦花朝節、鄉村振興交流會等活動,聯動高校打造“詩教潤鄉土”項目,將歐陽修文化融入景觀設計與研學課程。
塑造新時代的“傳統村落”
當古村風貌得到修繕恢復、市場運營駛入良性軌道,如何避免一些地方鄉村文旅“速紅速衰”的通病,實現長久繁榮,是釣源下一步令人關注的議題。
有專家認為,迎合遊客對新奇追求的“爆火”是非自然、刺激性的亢奮,熱鬧一陣後,隨着年輕人興趣點的轉移,剩下的只有一片狼藉。創新要“心中有根”。
與此同時,對古村落的保護也必須保持開放、包容的創新思維。復旦大學國土與文化資源研究中心主任杜曉帆教授認為:“變化是必然的,我們要警惕的是一些旅遊開發模式和消極的觀念,比如希望停止甚至是凍結遺產、村落和景觀變化,讓村民永遠生活在‘過去’。”
他說,最好的活態保護或活化利用,不僅僅是寄託一種懷舊情緒或將之轉化為商品進行消費,而是讓遺產迴歸村民的日常生活實踐中,激發社區的文化創造力,塑造新時代的“傳統村落”。應以精細化政策和制度設計,引導農二代、農三代等參與文化遺產保護。
“95後”張娜原來在外打工,現在回鄉擔任古村運營策劃。農家樂主人歐陽曉斌30多歲,這位歐陽氏的後人性情淳樸,燒得一手好菜。“之前在自家老房子裡開餐館,面積小不說,客人也不多。村裡改造後,現在有個三層小樓,最少可以擺下個五六桌,還有包廂。火的時候一天能掙6000多元。”
釣源的“蝴蝶返鄉”計劃令人矚目。其宗旨是形成“原住民+新村民”共治模式,定期舉辦研討交流會等學習活動,大力培育新型職業農民和鄉土人才。景區內大小商店、手工作坊均注重將創業青年、本土鄉賢、非遺傳人引流回村創業。元宵祭祖、舞龍表演、國際象棋賽事等活動賦予古村持續生命力,吸引專業人士和新農人聚集。
釣源引發很多到訪者感慨:城市或許並非現代人的終極目的地,不斷更新的鄉村,除了作為情懷的載體,也有可能成為理想的多元生活選項。
十里芳菲董事長張蓓說:“我做釣源項目,初意非常樸素。我是一個喜歡鄉村生活的城裡人,很想過歸田園居的生活,想生活在一個雞犬相聞、有好食材、有好鄰居的村子。我們這一群人把自己定義為釣源的新村民,願意與本地村民一起建設美好鄉村。”
農事節氣、田野風光、耕讀傳家的祖訓、鄰裡守望的民俗……這些中華文化的鮮明標識散佈在廣大鄉村。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加強鄉村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和活化利用。
尹冬苟說:“我理想中的釣源,未來應該成為一個宜居宜業、多元豐富的新型古村落,讓老村民與新村民共同在這個‘可以讓身體停下來等一等靈魂’的地方擁有美好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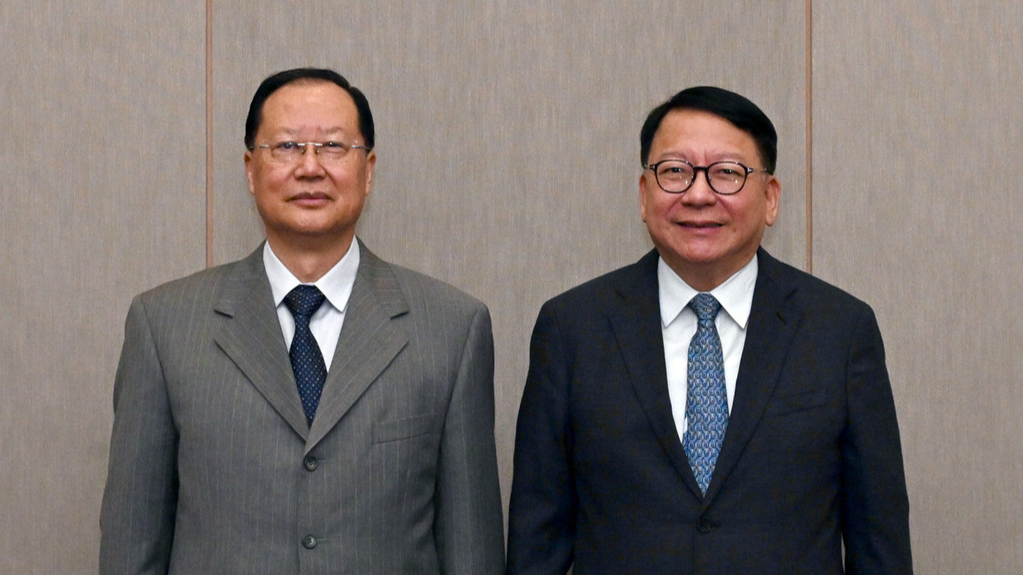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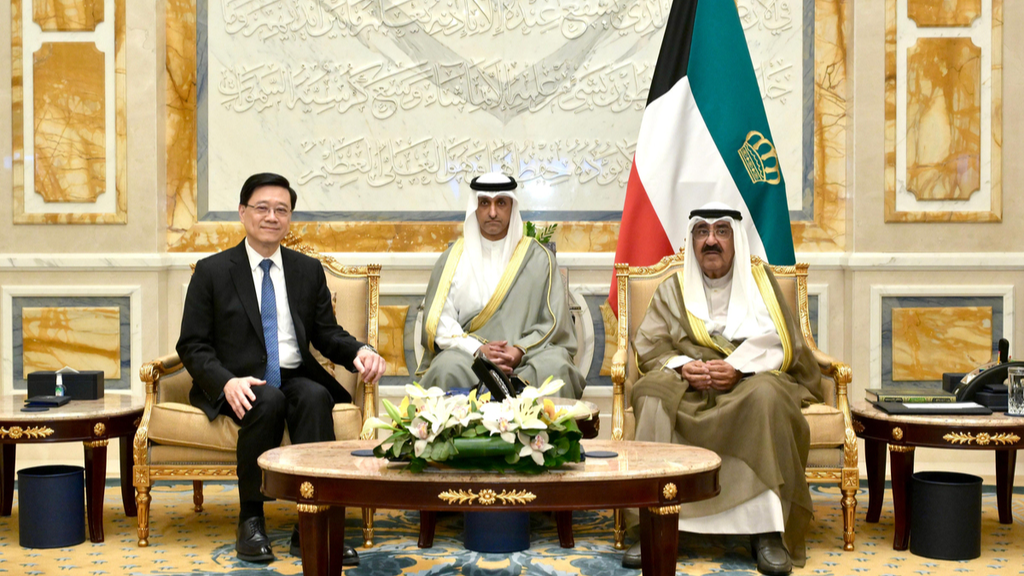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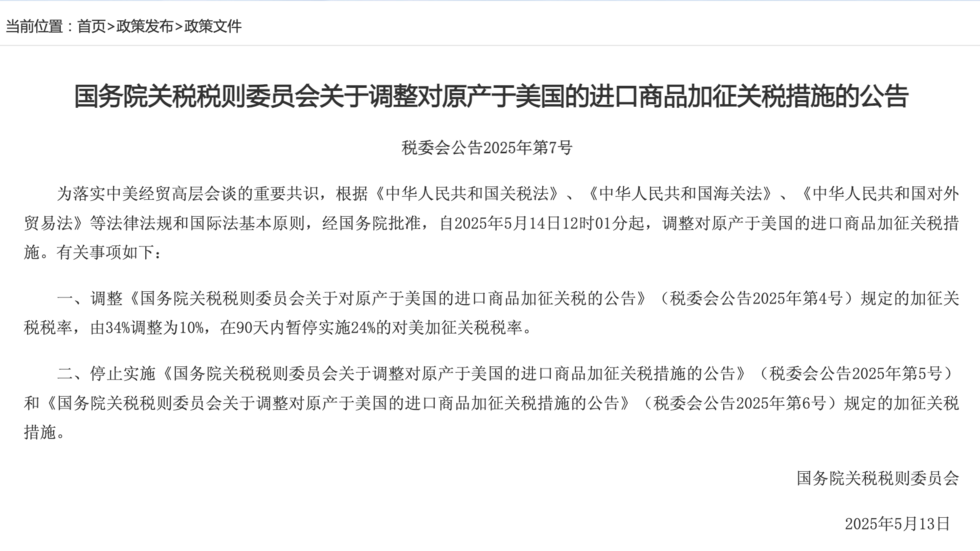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