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王 賀 | 溫州理工學院教授
本文深入探討了香港青少年與傳統儀式之間的緊密聯繫,分析了傳統儀式在個人成長、文化認同和社會聯結方面對香港青少年文化認同建構的深層意義。傳統儀式在個人成長中幫助青少年具象化習得倫理價值觀,培養心理韌性,激發創造力;在文化認同方面,傳統儀式助力香港青少年構建從「香港人」到「中華文化傳承者」的雙重身份轉變,提升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感;促進多元文化共生認知,實現歷史記憶活態傳承;在社會聯結維度,傳統儀式彌合代際隔閡,增進社區凝聚力,關注弱勢群體。總體而言,傳統儀式對增強香港青少年的文化認同具有重要意義,是文化傳承創新的關鍵力量。
在全球化和數字化的雙重衝擊下,傳統儀式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老一輩傳承人的凋零、年輕一代興趣的轉移、功利主義對文化價值的消解。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融的樞紐,傳統儀式的存續問題尤為典型。根據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以下簡稱「非遺辦」)的資料,香港於2017年公布的《香港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中共收錄了480項非遺項目,涵蓋表演藝術、節慶活動、傳統手工藝等類別。然而,其中近三分之一的項目面臨「傳承人斷層」的危機。
在這一背景下,促進香港青少年成為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和發展者,不僅是香港現代化轉型的核心推動力,更是增強文化認同的有效途徑。本文從個人成長、文化認同、社會聯結三個層面出发,結合香港本地案例,系統剖析傳統儀式對建構香港青少年文化認同的深層意義。
個人成長:在儀式中構建完整人格
傳統儀式是一個通過重複性實踐與象徵性展演來深度參與個體人格建構的過程。心理學家埃里克森(Erikson, 1968)提出,人格發展需經歷「認同與角色混亂」等關鍵階段。儀式通過社會角色賦予和連續性體驗,強化個體的自我同一性。社會學家布迪厄(Bourdieu, 1977)也認為,人的「慣習」(Habitus)是結構化社會行為傾向的重要因素。傳統儀式通過身體「慣習」(如跪拜、舞動),將文化資本刻入身體記憶,成為人格建構的文化基礎設施。在個體層面,它整合自我認知、道德結構與潛意識原型;在社會層面,它生產集體人格與代際慣習。當面對現代性對人格同一性的衝擊,傳統儀式為個體提供了穩定的「意義座標系」。
(一)倫理價值觀的具象化習得。傳統儀式通過行為符號傳遞抽象的道德規範,為青少年提供「可觸摸」的倫理課堂。在孝道與家族責任的具身實踐中,梅洛-龐蒂(Merleau-Ponty, 1945)的具身現象學揭示,儀式空間(如祠堂)與動作(如叩首)構成「身體圖示」,使抽象「孝道」概念被轉化為可感知的倫理實踐。儀式中的代際協作(長輩示範祭品擺放)通過鏡像神經元機制(Rizzolatti & Craighero, 2004)強化責任傳遞。香港圍村至今保留的「點燈儀式」(為新生男丁在祠堂掛燈籠),要求青少年參與祭祖、跪拜、族譜登記等流程。這一過程將「血脈延續」從概念轉化為行動,強化了個體對家族共同體的歸屬感。2022年對元朗鄧氏宗族的田野調查顯示,參與過點燈儀式的青少年中,83%表示「更理解長輩對自己的期望」。
在生命教育的自然滲透方面,香港的盂蘭勝會強調報答雙親養育之恩,體現了中國人對祖先的敬重和追思。盂蘭勝會通過施食、誦經等儀式,希望普度生命,讓它們得到解脫和安寧,體現了佛教慈悲為懷、眾生平等的理念。作為極具規模和特色的民間活動,香港的盂蘭勝會除了傳統的祭祀儀式外,還會搭台演戲,上演神功戲,吸引眾多市民和遊客觀看;飄色巡遊等活動展現了濃郁的地方文化特色;「燒街衣」和「撒米飯」行為暗含對生死的敬畏。2021年,香港道教聯合會推出「青少年盂蘭文化工作坊」,通過模擬祭祀場景,引導青少年討論環保祭祀、數字遺產等議題,將古老儀式轉化為現代生命教育的載體。
(二)心理韌性的儀式化培育。美國社會學家安妮.斯威德勒(Ann Swidler,1986)在《文化在行動中:符號與策略》(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一文中提出文化工具箱理論。該理論認為,文化並非提供行為的最終價值或目標,而是提供一套習慣、技能和風格,人們可以從中構建「行動策略」。通過參與傳統節日、慶典活動、民俗儀式等,青少年能夠在親身實踐中感受傳統文化的魅力,從而建立平衡的心理狀態;傳統儀式中的故事和寓言富含心理教育意義,能夠幫助青少年學習如何處理情緒、面對挫折等。
在香港,驚蟄「打小人」這一習俗最早可追溯至古代的「厭勝之術」,是一種利用咒術或法器來祈求神靈降福、驅邪避害的巫術,最初與農業社會相關。相傳驚蟄時春雷始鳴,驚醒蟄伏的害蟲,農民會用鞋子打走害蟲,也會祭拜白虎鎮壓害蟲,後逐漸演變成習俗「打小人」,寓意擊退小人、求諸事順利。隨著時間推移,「打小人」在香港不斷傳承和發展,從最初帶有一定詛咒性質的巫術,逐漸演變成現代人心理慰藉和情緒宣泄的方式,成為頗具特色的民間儀式。2014年,「打小人」習俗被列為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一看似荒誕的習俗,實則為情緒管理提供了隱喻性解決方案。香港大學2023年的一項研究指出,參與過這一習俗的青少年群體焦慮指數平均降低了17%,因其能夠通過「轉移攻擊對象」的象徵行為釋放壓力。
在香港的宗教文化景觀中,黃大仙祠的「求簽—解簽」機制佔據著獨特地位,散發著深厚的文化魅力。它不僅是簡單的儀式,更是無數人心靈的避風港,為人們在紛繁複雜的生活中提供精神寄托和心理慰藉,同時也是香港歷史文化與民間信仰的生動映照。譬如通過求取「學業簽」的過程,青少年可以明白學業之路並非孤立無援,自身的主動努力亦至關重要。當他們依照建議,積極向教師請教,收獲知識與進步時,便開啟了「努力—反饋」的正向循環。每一次主動付出帶來的學業提升,強化了他們的自信與動力,促使他們更積極地投入學習,在傳統宗教文化習俗與現代學習生活之間搭建起一座促進成長的橋樑。
(三)傳統技藝中的創造力覺醒。非遺技藝的傳承過程本質上是創造性思維的訓練場。非遺技藝領域有著獨特的規則與符號系統,傳承者在傳承過程中不斷與領域知識互動,結合時代需求創造新作品,這一過程得以激發傳承者創造性思維,使其不斷突破傳統框架,從材料選用、製作流程到呈現形式,都可能因創造性思維產生革新,推動非遺技藝的傳承與發展,讓古老技藝在新時代煥發新魅力。
在香港長洲太平清醮的「包山架紮作」中,傳承者需掌握竹編、力學、色彩搭配等技能。作為一項古老的傳統技藝,包山架紮作通過代代相傳,保留了獨特的紮作工藝和技巧,如對材料的選擇、竹子的加工處理、骨架的搭建等,它們作為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承載著長洲的歷史記憶和文化傳統,反映了當地居民長期以來的生活方式、信仰習俗和價值觀念,是了解長洲歷史文化的重要窗口。掛滿平安包的包山象徵著對祖先和神靈的供奉,人們通過這種方式祈求神靈庇佑,消災解難,保佑長洲地區風調雨順、居民平安健康。2023年,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將包山架結構融入建築模型課程,學生設計的「可拆卸環保包山架」獲紅點設計獎,更加證明傳統技藝能夠激發跨界創新。
香港大坑舞火龍所需的「香枝插製」工藝正通過3D建模和AR技術實現標準化教學。香枝插製工藝是大坑舞火龍這一傳統民俗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承載著歷史記憶和文化內涵。通過代代相傳,保留了獨特的手工技藝,如香枝的選擇、插製的方法和技巧等,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元素,延續了地方文化的脈絡。它見證了大坑地區的歷史變遷和文化發展,反映了當地居民的生活方式、信仰習俗和價值觀念。作為活態文化遺產,香枝插製後的火龍被視為吉祥之物,具有驅邪祈福的寓意。香枝燃燒時散發的香氣和火光,被認為可以驅趕邪惡、瘟疫和不祥之物,為當地居民帶來平安、健康和好運。青少年在「火龍數字孿生系統」中實驗不同插法對燃燒效果的影響,傳統匠人的經驗得以轉化為可傳播的數據邏輯。
文化認同:在全球化浪潮中錨定自我
吉登斯在《現代性與自我認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1991)中提出:在傳統社會中,文化認同通過「自然繼承」(inherited traditions)實現,個體嵌入穩定的社會結構與地方性知識中,認同是「既定的」(given)。然而,現代性(尤其是全球化)導致傳統斷裂,個體被迫通過「反思性規劃」(reflexive project)主動構建自我認同,這一過程充滿不確定性。現代社會的「脫域機制」(disembedding mechanisms)將社會關係從地域性情境中抽離,導致個體陷入「存在性焦慮」(existential anxiety),即對身份歸屬的持續不安。
(一)雙重身份的構建:從「香港人」到「中華文化傳承者」。香港青少年的文化認同具有獨特的層級性。阿爾君.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1996)提出全球化文化流動的五個維度(景觀):族群景觀、技術景觀、金融景觀、媒體景觀與意識形態景觀。香港青少年通過本地儀式抵抗全球文化同質化,將族群景觀(地方信仰)與技術景觀(社交媒體傳播)結合,形成「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認同策略。
本地符號的屬地化凝聚。以銅鑼灣大坑村的舞火龍活動為例,這一傳統活動最早可追溯到19世紀。當時,大坑地區瘟疫橫行,村民依照中國民間習俗,以舞火龍驅趕瘟神。多年來,這一活動承載著大坑村的歷史變遷和先輩們與災難抗爭的記憶,成為傳承歷史的重要載體,讓村民銘記過去的艱難歲月以及先輩們的智慧和勇氣,成為大坑村獨特的文化符號,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通過參與和觀看舞火龍,青少年能夠深刻感受本地文化的獨特魅力,從而更加珍惜和保護自己的文化傳統,增強地域文化的凝聚力。這些精神價值通過舞火龍活動代代相傳,成為香港青少年文化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激勵他們在現代社會中繼續保持團結奮進、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
建立國家認同的文化紐帶。2021年,香港教育局在中小學語文課程中增設93篇經典古詩文建議篇章,要求學校自2021年秋季起逐步加入這些篇章,並在2024/2025學年全面落實。為配合「建議篇章」的教與學,教育局持續舉辦各類教師培訓課程,製作相關書冊、資料等,並推出「中華經典名句網上自學平台」,讓中小學生通過網上遊戲及自學資源學習中華經典名句。
此外,香港教育局舉辦了多樣化的文化活動。比如,「華萃薪傳——全港小學中國歷史文化問答比賽」,自2021年首屆比賽成功舉辦以來,影響力與日俱增。2024年7月4日,「心繫家國」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7周年暨聯校國民教育活動匯演,通過以中國傑出歷史人物、飲食文化、茶藝及古詩美文等為主題的中華文化傳承和體驗活動,增強學生對中華文化和國家發展的認識。「香港故宮學生文化大使」計劃通過專題講座、實地考察、博物館導賞講解培訓等專題活動,讓學生增加對文物保護及博物館工作的認識,參與歷史文化遺產保護。
香港教育局同時資助到內地考察交流活動。2021年,教育局在全港高中全面推行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並將內地考察納入課程。2024/2025年度,教育局進一步發掘更多合適的參訪點,預算開支由8,260萬港元增至1.16億港元,組織香港學生到內地參觀交流,如「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教師考察之旅」「薪火相傳」國民教育系列活動等。數據顯示,參與這些儀式活動的青少年對「中國人」身份認同度提升了29%,證明儀式實踐能夠跨越意識形態差異,喚醒文化根源意識。
(二)多元文化共生的認知啟蒙。香港作為文化熔爐,其傳統儀式本身就是一本多元共存的教科書。從歷史角度看,香港在古代便受到嶺南文化的滋養,其傳統節慶儀式帶有濃厚的嶺南特色,如春節期間的舞獅活動遵循嶺南傳統的舞獅套路、配樂和儀式流程,從點睛到採青,每一步都蘊含著驅邪納福、吉祥如意的寓意,這是本土文化傳承的重要體現。
英國殖民統治時期,西方文化不斷湧入,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儀式在香港生根發芽。聖誕節時,教堂舉辦的彌撒儀式,從唱詩班的頌歌到信徒的虔誠禮拜,又與西方基督教國家的慶祝儀式一脈相承。在香港島中環地區,既有傳統中式廟宇如文武廟,舉行祭祀儀式,人們焚香祈福、遵循傳統祭典程序,香煙繚繞間彌漫著中式傳統信仰的莊重;又有西式建築風格的聖約翰座堂,舉行婚禮、禮拜等宗教儀式,彰顯西方宗教文化。兩者在空間上相鄰,同時各自保留著獨特的儀式傳統,互不干擾又和諧共生。
民間信仰的實用主義課堂。香港車公廟堪稱一處宗教文化交融的獨特場所。廟內佛教觀音慈悲端坐,象徵慈悲與救苦救難;道教呂祖仙風道骨,代表道家的智慧與超凡境界。觀音以其大慈大悲的形象,常被人們祈求庇佑心靈、護佑平安;呂祖則在人們面臨抉擇、尋求智慧指引時,成為心靈寄托;車公則在驅邪避災、保佑出行等方面發揮作用。此種「功能性信仰」對青少年成長具有特殊意義,樸素的宗教觀讓青少年在面對多元價值選擇時,不會感到迷茫無措,而是依據自身實際情況作出理性選擇,逐漸培養獨立思考和價值判斷的能力。
中西節慶的對話性共存。在香港這座文化多元的城市,萬聖節與盂蘭節的特色活動常在相近時段出現,形成獨特的文化景觀。萬聖節時,大街小巷滿是裝扮各種鬼怪、形象各異的人群;盂蘭節期間,傳統祭祀儀式莊重舉行,人們懷著敬畏之心,通過儀式祈求平安,驅逐災禍。
對青少年而言,兩種截然不同對待「超自然力量」的文化理念和態度,猶如兩扇通往不同文化內核的窗口。在萬聖節的「扮鬼」狂歡中,他們體驗到的是一種對超自然元素的娛樂化演繹,通過誇張的裝扮和歡樂的氛圍,展現對未知神秘力量的輕松調侃,反映出西方文化中對死亡議題相對豁達、敢於以幽默和娛樂化解恐懼的態度。於盂蘭節的「驅鬼」儀式,青少年看到的是長輩們嚴肅認真的神情,以及一系列遵循傳統的莊重祭祀流程,從中深切感受到的是東方文化中對超自然力量的敬畏,體會人們對死亡的敬重和祈願。
香港聖保羅男女中學敏銳地捕捉到這一獨特文化現象並將其融入跨文化課程中。教師巧妙引導學生設計「中西鬼節對比手冊」。在此過程中,學生們不再把兩種節日的差異視為衝突,而是當作寶貴的學習資源。他們深入研究萬聖節與盂蘭節的起源、傳統習俗、象徵意義等各方面的不同,分析背後所蘊含的東西方生死觀和價值觀。通過對比學習,青少年拓寬了自身的文化視野,學會了站在多元視角看待世界,理解不同文明面對死亡議題時各自獨特且值得尊重的回應方式,不僅提升了文化素養,更培養了包容的胸懷,為日後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好適應多元文化環境奠定了堅實基礎。
(三)歷史記憶的活態傳承。儀式是抵抗歷史虛無主義的「疫苗」。從文化記憶理論視角看,儀式承載著特定群體的歷史記憶與文化內涵,每一場儀式都是對過去的回溯與傳承;從社會學理論出發,儀式具有社會整合與規範功能。群體共同參與儀式,對共同歷史和價值觀的認同將得到強化。
長洲太平清醮儀式起源於清朝時期一場肆虐的瘟疫。長洲居民為祈求平安、驅散瘟神舉辦了盛大的祭祀儀式,形成了長洲太平清醮的雛形。隨著歲月流轉,這一傳統活動不斷發展演變,其飄色巡遊環節如今尤為引人注目。在飄色巡遊中,孩童們精心裝扮成各類歷史人物,身著華麗服飾,神情靈動。他們或是演繹古代英雄的英勇事跡,或是重現歷史典故中的經典場景。
2020年全球遭遇新冠肺炎疫情衝擊,長洲青少年展現出非凡的創造力與文化傳承精神,自發創作了「口罩飄色」,延續傳統飄色形式,高高站在精心裝飾的花車上。與以往不同的是,他們都戴上了口罩,所扮演的角色也融入了抗疫元素:有的扮成醫護人員,展現一線抗疫人士的無畏身影,有的則化身志願者,傳遞互助友愛的溫暖力量。「口罩飄色」的出現,巧妙地將傳統與現實緊密相連,實現了歷史與現實的深度對話。前輩們的抗疫精神激勵著當今青少年勇敢面對疫情,青少年的創意之舉也為長洲的歷史文化注入了新內涵,讓長洲的集體記憶在傳承中不斷豐富、延續。
香港仔的天后誕是一場承載著深厚海洋文化與地域記憶的傳統慶典,其中的「漁船掛幡」儀式尤為矚目,宛如一條時光紐帶,將香港的過去與現在緊密相連。天后誕期間,一艘艘漁船整齊排列,桅杆上懸掛著色彩斑斕的幡旗,在海風的吹拂下獵獵作響,訴說著往昔的故事。幡旗上的北鬥七星圖案看似簡單,實則蘊含著古老神秘的智慧。對於青少年而言,這一圖案成為他們探索歷史的起點,進而追溯到宋代《萍洲可談》中記載的航海導航技術。彼時漁民通過觀測北鬥七星的位置來確定船只航向,穿越茫茫大海,駛向未知的遠方。對幡旗圖案的研究過程則是一種「考古式參與」。青少年不僅是儀式的旁觀者,更成為了歷史的探索者,通過對「漁船掛幡」儀式中幡旗圖案的研究,深刻理解香港的轉型並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傳承與發展中,不斷適應時代需求的結果。「考古式參與」讓青少年在了解香港歷史文化的同時,也對家鄉的發展歷程有了更為深刻、全面的認識,增強了他們的歸屬感與認同感。
社會聯結:重建數字時代的溫情網絡
數字時代,人們的社交模式發生了深刻變革。社交媒體等即時通訊工具讓溝通跨越時空,看似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但在一些特定情況下,人們在享受數字便利之時,內心也易感到孤獨。從社會學視角來看,社會聯結是個體與群體社會形成的各種關係紐帶,對個體心理健康和社會穩定運轉至關重要。
(一)代際隔閡的儀式性彌合。在數字時代,技術反哺為家庭關係帶來新變化,其中以權力平衡的動態調整尤為顯著。以春節期間香港的「電子揮春」製作為例,這一新興活動巧妙成為代際合作的絕佳契機,重塑了家庭內部的權力結構。
傳統上,書法技藝多由長輩掌握,憑借深厚功底與多年經驗,他們成為傳統書法美學的傳承者與權威。激光雕刻機這類新興數字技術設備對熟悉傳統紙筆書寫的長輩充滿挑戰,卻是青少年的優勢所在。製作「電子揮春」時,長輩向晚輩悉心傳授書法美學,延續文化傳承責任;青少年則發揮對數字設備的熟練操作能力,幫助長輩使用激光雕刻機,將書法作品精準轉化為電子形式,實現傳統與現代的融合。深水埗的「數碼耆英計劃」有力證明了此種代際合作的積極影響。數據顯示,共同完成傳統工藝的家庭的代際衝突發生率降低了42%。合作過程中,雙方在技術與傳統的交流中相互學習、相互依賴,家庭權力實現了更為均衡的分配,不僅提升了家庭凝聚力,更讓傳統工藝在現代技術助力下煥發生機,促進家庭關係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更加和諧穩固。
新界圍村「盆菜宴」的籌備中,青少年負責採訪長者,記錄食譜故事,最終匯編為《盆菜裡的家族史》。這種參與式記錄讓青少年的參與從「被動聽故事」轉為「主動建構記憶」。在新界圍村,盆菜宴不僅是一場美食盛宴,更是承載著家族記憶與歷史傳承的重要文化活動,在籌備過程中,口述歷史的場景化激活為青少年提供了獨特的文化學習與傳承體驗。採訪過程中,青少年們深入圍村的各個角落,與長者們圍在一起,這些故事在廚房的煙火氣中、食材的處理間生動地展開,不再是書本上枯燥的文字,而是鮮活的生活場景。這一過程中,青少年從單純的聽眾轉變為群體記憶的主動建構者,不再被動地接受家族歷史,而是通過自己挖掘、整理那些被歲月塵封的故事,賦予家族記憶新的生命力。
(二)社區歸屬感的儀式培育。在香港大澳,端午龍舟遊湧是極具地域特色與文化價值的傳統活動,神艇則是其中的關鍵元素。這一活動需要漁民、消防員、學生等多方攜手,共同拖神艇巡遊水道,是維繫社區文化傳承與精神哺育的紐帶。2018年,台風「山竹」凶猛來襲,給大澳帶來重創,部分承載著信仰與傳統的神艇被無情摧毀。面對這一困境,大澳青少年迅速發起眾籌活動,藉助社交媒體、網絡平台等渠道,詳細介紹神艇受損狀況及修復的重要意義,呼籲社會各界伸出援手。行動引發強烈反響,眾多愛心人士紛紛慷慨解囊,提供資金支持。過程中,漁民憑藉自身對神艇結構和製作工藝的了解,承擔起技術修復的重任;消防員發揮專業優勢,利用繩索、起重機等工具,協助搬運沉重的神艇部件,保障修復現場安全有序;學生們積極參與,幫忙清理神艇表面污垢、繪製裝飾圖案等。
盂蘭勝會的「派平安米」活動由來已久,多是在特定地點集中發放平安米,承載著向民眾傳遞平安、祈福的美好願景。近年來,青少年積極參與,為其注入關愛弱勢群體等新的內涵,比如「派平安米」活動中加入了「送餐到獨居老人」的環節。在籌備階段,青少年深入社區,通過與社區工作人員合作、挨家挨戶詢問等方式展開調查走訪,精準定位需要幫助的獨居老人;確定名單後,策劃送餐流程,合理安排時間與路線;每到送餐日,青少年手提裝有餐食的袋子,穿梭於大街小巷,將飯菜送到老人手中。在送餐過程中,青少年陪老人聊天,傾聽他們的心聲,關注老人的居住環境,了解他們日常生活中的困難並及時反饋給有關方面。這一創新的慈善形式,重新定義了傳統的「派平安米」活動,讓其不僅僅是物質的給予,更是情感的傳遞與關懷的延伸。這一行動成功推動社區聚焦隱形貧困問題,讓弱勢群體獲得了更切實更豐富的關懷與幫助。
結 語
對香港青少年而言,傳統儀式並非僵化的歷史遺留,而是一座蘊含無限可能的文化基因庫,他們以現代視角拆解傳統元素並加以重新組合。參與傳統儀式,為香港青少年提供了個體成長的堅實錨點,在學習和參與傳統儀式的過程中找到身份認同與歸屬感。青少年利用數字技術記錄傳統儀式並進行全球傳播,展現出以創新方式推動中華文明與時俱進及其在現代社會中的持續發展。香港青少年在傳統儀式傳承中的實踐,為文化傳承提供了範例,證明文化傳承需順應時代發展,不斷創新演繹,才能在不同時代綻放獨特魅力,延續文化生命力。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5年4-6月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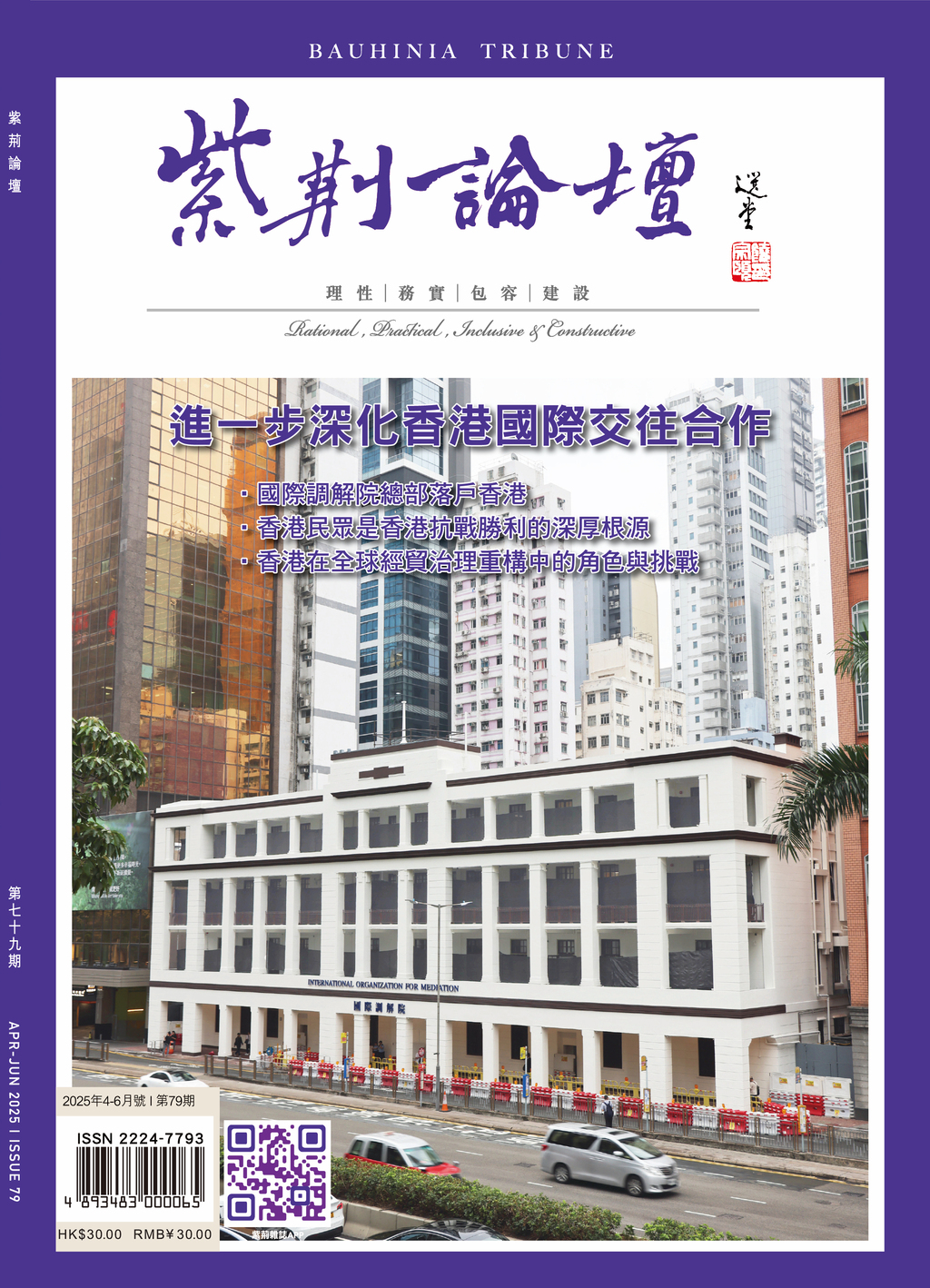







 今日熱搜
今日熱搜

 本週熱搜
本週熱搜

 本月熱搜
本月熱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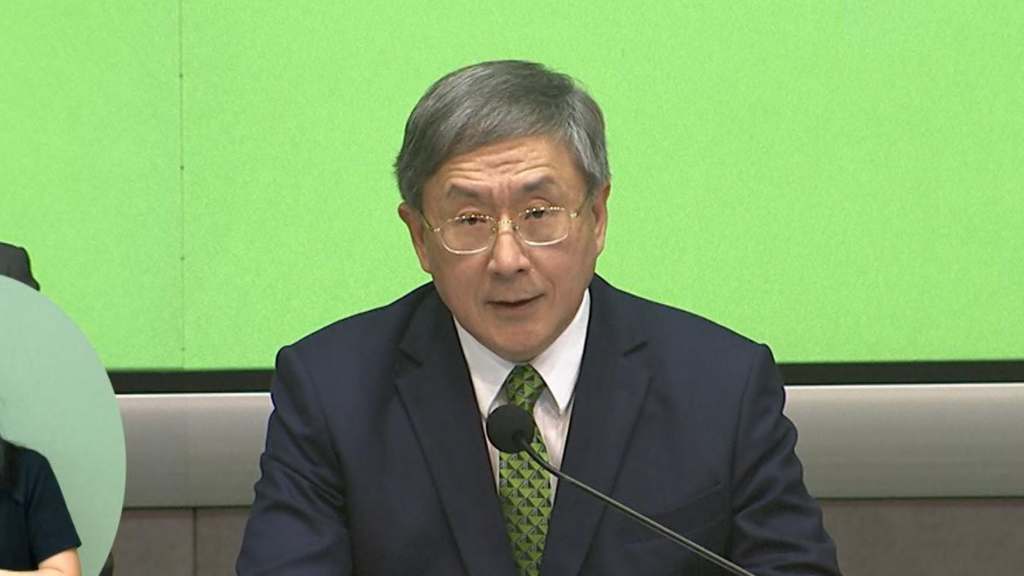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