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陳學然 |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教授及副系主任
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的時刻,我們不能忘卻當年香港上百萬市民經歷的戰火苦難。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是香港史上稱作「三年零八個月」的日軍佔領歲月。在此期間,日佔政府施行高壓統治,人人自危;加上物資短缺,糧食不足,民眾被逼離港歸鄉,無業者則被押送至無人島活生生餓死。留下的民眾無不掙扎求存,說是人間煉獄,實不為過。然而,在這最為黑暗的時刻,香港不乏民眾參與抗日救國行動,留下不少抗戰史蹟與救國故事。回顧歷史,不只是要新一代認識香港曾經有過這樣一段黑暗、痛苦的歲月,同時也是要緬懷先烈的壯舉;銘記歷史,不是要記住仇恨,而是要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日子,並且時刻保持居安思危的警覺性。
黑夜來臨前:港人反日救國運動受港英政府打壓
英國於上世紀初與日本簽訂「英日同盟」條約,規定兩國在遠東的合作關係,包括雙方在所屬轄境內互保雙方利權。該條約雖於1923年失效,但二者既合作又猜忌的關係一直延續。日本日益強盛的國力,使英國為之忍讓,避免自身在華利益受損。故此,香港居民的反日救國運動,長期受到港英政府打壓。五四運動、濟南慘案、「九一八」悼念殉國同胞活動,香港市民奮勇上街抗議日軍惡行的義舉都受到港英政府打壓。直至香港淪陷前,香港報刊但凡出現抗日、批評日寇的標題或文章,都受制於港英政府新聞審查條例,或不准刊載或大幅度地以「打天窗」形式見報。
1930年代中後期,港英政府當局兩手準備,一方面壓制反日言論,一方面因應日軍的廣東軍事行動而加強防務,建立起號稱東方馬奇諾防線的「醉酒灣防線」,也在要塞位置加建機槍堡、炮台等工事。但是,這一切相比日軍的強大兵力,薄弱得不堪一擊。香港防務的缺陷問題,與英國把亞洲軍力回調至歐洲主戰場有莫大關係。即使英國當局意識到日軍可能犯境,最後也只能讓萬餘「雜牌軍」防守香港;當中包括千餘名華籍英兵外,逾百萬華人雖然熱心於支援抗戰救國,但對於香港存在怎樣的日軍威脅毫不知情。英國無意派駐正規軍增援,在於不欲把有限資源浪費在香港這個不可能守住的地方。故當日軍一旦進犯,英國軍民可以做的只是爭取儘快撤離香港。那麼,死守香港島以待救援或撤離,成為了港英政府的基本戰略考慮。香港人口中佔比95%以上的中國人,長期來得不到港英政府信任,一直被排除於政府體制外,以致港英政府防務是否得當,備戰是否充分,他們都沒有置喙之餘地。香港社會上下不能團結、難以齊心,快速淪陷不是什麼意外之事。

國家有難,香港絕大部分居民表現出熱烈的救國熱情,投入抗日救國的籌款、認資活動。香港各大商會與東華三院自「七七事變」以來,便為受影響軍民籌款救濟。由華人領袖周壽臣擔任要職的救國公債勸募委員會香港分會,籌得逾五百萬港元善款。就連貧苦低下階層市民也節衣縮食,合力義賣;1938年8月,小販發動的籌款更高達百萬港元。其他華人領袖眷屬如羅文錦夫人、李樹培夫人成立香港中國婦女會,組織香港婦女參與救國慈善工作。影藝界、教育界、南來文人團體,紛紛組織籌款賑濟活動,以人道救援之名行抗日救國之實。宋慶齡與政商要人則藉助香港創辦了保衛中國同盟,發起「一碗飯運動」,大力呼籲海外華僑抗日救國。八路軍更在香港成立了辦事處,由廖承志擔任主任,為中國抗戰作出巨大貢獻。
然而,港英政府在日軍威脅日深之際,也加強了中文報刊審查工作,限制華人公開發表抗日言論。英國對日妥協讓步,一廂情願地把處於中日戰爭邊緣的香港定位為「中立」角色,求取香港免受軍事進犯。為穩定民心,港英政府公開宣稱香港是安全的,強調英軍有能力保護香港。港英政府的表態,讓香港某些人對於英軍的防守能力與抵抗決心過於樂觀。但這些反過來使香港社會整體的備戰意識不強,一些南來香港的富貴「難民」更是醉生夢死,寄情於聲色犬馬,使淪陷前夕的香港呈現一片紙醉金迷的假象。1941年11月,香港各大報紙最矚目的是「劉美美」案。該案涉及英國將領在一宗防空工程上的賄賂事件,中間人劉美美與該將領有染,其豪奢生活與桃色關係成為案件最大新聞,被市民當作茶餘飯後的談資。只是,人們對於逾六萬日軍陳兵港深邊境的事實,卻是置若罔聞。
1941年12 月,香港瀰漫著慶祝聖誕節的歡慶氣息。12月6日,就在陷入日軍佔領的最後一個周末,跑馬地照常賽馬,甲組足球聯賽如期熱烈舉辦。12月7日星期天,市民奔往皇后戲院觀賞《英宮十六年》,外藉人士如常在私人會所參加各種球類活動與海上活動。唐海《香港淪陷記》的第一章《寧靜的星期日》指,香港沒有人會想到戰爭即將於第二天清晨來到,而他們都沉醉於最後的一個休假日。在這個假日裡,人們的安閒──「表現在電影院滿座,酒吧間堆滿了客人,舞場裡不停的發散著爵士音樂上,四周找不出一絲的戰爭氣息;只是近二三天來香港政府在舉行開玩笑般的防空演習而已」。1941年12月8日早上七時,48架日本軍戰機空襲香港啟德機場,五分鐘內炸毀香港僅有的五架軍機和八架民航機,其他軍事據點與交通設施,無一倖免。六萬日本陸軍兵分兩路從上水及錦田向市區推進,醉酒灣防線於12月10日因兵力薄弱而被日軍攻破,日軍打開了通向九龍市區的大門。
對於大多數香港居民而言,生活世界的徹底改變,比預期的來得更為突然、更為痛苦。
日軍登陸:人間煉獄,惶恐終日
1941年12月18日晚,日軍於北角一帶登陸香港島,與英軍相繼在黃泥涌峽、淺水灣激戰。12月22日,跑馬地為日軍所佔,爆發了屠殺平民的「藍塘道慘案」。死者包括了最早響應「五四新文學運動」在香港發展的「策群義學」成員屈柏雨,他是香港著名教育家梁省德的丈夫。他當天正在華人領袖鄧肇堅的藍塘道大屋作客,屋內共計48名男性被殺害,包括鄧肇堅妻子在內的女性慘遭凌辱。根據日軍攻佔香港指揮官酒井隆的判決書所述:「(1941年12月22日)同月二十二日下午六時,在藍塘道二號,屠殺居民四十八人,並姦殺孕婦,輪姦年甫十二三歲之幼女,洗劫財物而去。」在日軍攻佔香港期間姦淫虜掠,地痞流氓也趁亂肆虐百姓,燒殺搶掠,洗劫平民,社會完全失序失控。
12月25日傍晚,港督楊慕琦和駐港英軍司令在日軍司令部半島酒店正式簽署投降協議,香港史將當天稱作「黑色聖誕」。12月28日,日軍分別在九龍彌敦道與港島軒尼詩道舉行勝利入城儀式。日軍在儀式後四處狂歡慶祝,這是香港居民經歷噩夢的伊始。日軍四處搜刮物資、尋索女人。日軍中將酒井隆後來招供,他自率領部隊進駐港島後之半個月來,縱容部屬「實行大規模之屠殺姦掠,藉以報復,而逞淫威。」又據唐海記述:「他們三二個一起,敲打隨便那一家的門戶——這幾個晚上,許多女人嚇得在三四層樓的屋頂上亂跑,瓦片被踏得發出破裂的聲音,很多女人遭到了侮辱,他們有被三個敵人一起輪姦的」。聖士提反書院傷兵醫院裡的170名傷兵,即使是投降了,也全部遇害,而七、八名護士則難逃被姦殺的惡運。
用「人間煉獄」形容淪陷後的香港境況,絕不為過。著名詩人戴望舒因從事抗日活動而被捕入獄,他於域多利監獄受盡折磨。他的《獄中題壁》《我用殘損的手掌》《等待》諸詩,十分形象地描述其受到的虐打:
做柔道的呆對手,劍術的靶子,
從口鼻一齊喝水,然後給踩肚子,
膝頭壓在尖釘上,磚頭墊在腳踵上
聽鞭子在皮骨上舞,做飛機在樑上
蕩……
戴望舒還是幸運的一個,沒有慘死獄中。對於當時不少市民而言,人命賤如草芥,朝不保夕。日軍濫殺無辜的事件無日無之,血腥場面隨處可見。據當時人的憶述,一名小童在沒有挑釁日軍的情況下,被日本士兵開槍射中腹部,以至「腸臟溢出,已出現腹膜炎」,幸好小童母親懂日語,否則「會被日兵棄在路旁」,憶述者聲稱「這些事件不勝枚舉……」。另有中立國居民憶述乘坐渡輪過海時的所見所聞:「海裡全是漂浮發脹的屍體。市內已有太多屍體尚未埋葬,浮屍因此無人理會」。她也在回家路上看見多個男性華人被吊起綁在欄杆上,雙腳離地一呎。這些被打傷的人或已死去,或仍在垂死掙扎。她形容這種情況「舉目皆是」。如今讀此文字,仍教人觸目驚心。
香港淪陷期間,日本籍牧師鮫島盛隆恰好派駐香港。在他幫助下,香港聖保羅女書院逃過被日軍蹂躪的厄運。他筆下講述了日軍在港瘋狂行徑以及香港居民受到的深重傷害。其中一人便是香港女教育家、香港第一位女博士兼第一位獲得英皇勳銜的女性華人胡素貞。她作為聖保羅女書院(聖保羅男女中學前身)校長,鮫島指她下定決心捨命保護四十多名女學生,「不遭軍士的暴亂或強姦,她以這種悲壯的決意,盡力設法,掩護學生」,「保護她們不受像其他佔領區所頻頻發生的那種暴力凌辱」,這讓他深深佩服胡素貞的擔當與勇氣。然而,為了保護學生及校舍免受日軍蹂躪,胡素貞承受著極大的精神壓力。她因過於驚恐,三、四年下來,雙膝因顫抖而永久損傷,不能再上下樓梯,導致她後半生要依靠輪椅代步。
日軍的殘暴統治,對於時人的精神如何折磨、造成何等的傷害,從上可見一斑。
實行「歸鄉計劃」:草菅人命,餓殍遍地
日軍在香港先後成立軍政廳、總督部,暴力執行社會管控規例。《香督令》是香港佔領地總督磯谷廉介頒布的法令,內容細如牛毛,日軍可以隨意指控華人是否觸犯法例,當街打罵,甚或將之囚禁,乃至殺害。如果市民在街上沒有向站崗日軍行鞠躬禮,輕遭拳打腳踢,重則開槍殺害。憲兵隊更常以搜查抗日分子為藉口,擅闖民居,姦淫擄掠。
為了管制言論和消息傳播,所有新聞通訊及文化活動均遭嚴格審查。取而代之的,是當局強力移植日本文化,建立神社、築造忠靈塔,灌輸日本帝國意識和價值觀,向香港華人進行思想洗腦,實施赤裸裸的「日本化」文化侵略。以教育範疇為例,當局以日文取代中英文教育。華人辦學權利被剝奪,1941年香港學生人數約12萬人,至1945年僅餘3,000人,學校則由600所跌至20多所。香港固有的公元曆法被日本曆法(如「昭和」年號)取代,日本節慶(如天皇壽辰)被列作香港公眾假期。香港的時間被調快一小時,保持與日本時間同步並行。日本的街道名在香港也大行其道,港島的干諾道改為「住吉通」,德輔道改為「昭和通」,西環改為「山王區」,太子道改為「鹿島通」;英資連卡佛百貨公司改稱「松坂屋」,動植物公園改稱「大正公園」,半島酒店改名「東亞酒店」。「日本化」、「皇民化」的景象,於當時觸目皆是。
文攻武嚇,是日本佔領地總督府統治香港的基本方式。但對於管治香港這個地少人多的地方,單靠文攻武嚇在當局看來還是未能穩定香港的。太多的人口,會使這個地方產生很多問題。香港早於淪陷前,人口便已高達160多萬。太平洋戰爭一旦爆發,輸港物資停頓,糧食供應短缺。故當日軍從英人手上奪得香港統治權後,便開啟了「歸鄉計劃」,逐步遷移沒有固定職業或專業技能的平民離開香港。日軍為便於人口管治與糧食管制,設立住民登記證及離港通行證。一些從事機械作業、工廠、農業及生活必須品生產等固定職業,或者是軍方認為有需要的人士,得以留下。他們平時上街必須隨身攜帶住民證,否則要面對日軍當街隨意施加的軍罰。當局於1944年3月進行了嚴厲的戶口調查,若有人沒有整齊站在屋前街道候查而走出馬路,即被開槍擊斃。若家庭成員不齊,整家會被拉往刑訊。一次人口調查,便有數千市民被捕或被殺。
1943年後期,日軍在東南亞與中國的戰事相繼受挫,香港的貨運停頓,各種物資被日軍優先調運前線與日本本土。為控制糧食與物資,日軍採取殘暴的武力抓捕乞丐、無業遊民、流浪者,或把他們遣送至離岸孤島自生自滅,或將他們強行押解出境,甚至是半途棄置,釀至多人餓死、病死或因風暴葬身大海。小林英夫指出:日軍「將處於弱勢的老人、婦女、兒童遺棄到偏僻的小島或者人跡罕至的中國沿岸地區。以一天減少1,000名中國人為目標,在佔領香港一個月的時間就讓23,000名華人慘遭如此命運。 」
一些身體健壯的勞工,被運送至海南島開採鐵礦,他們在惡劣條件下因疾病或虐待而死亡,五萬人中有四萬五人因工作過勞或被日人虐待致死,還有120名華工被日軍刺死。1941 年 12 月至 1943 年 9 月,近 100 萬人被強制遣返,香港人口因而驟降至戰前的一半。至1943年底,香港人口急降至80萬,1945年日本投降時則僅餘50至60萬人。進言之,香港於日佔期間每月平均減少二萬三千人,而1945年的首八個月出生率則只有三千七人,說香港成為死港,實不為過。
1943年後期,香港經濟瀕臨崩潰,萬物通漲幾近失控。日軍把香港居民原有的銀行存款凍結,以軍票全面替代港幣。1941年 12 月底是 1日圓兌換2港元,大半年後即調升至 1日元兌換4港元。日軍禁止港幣流通,強制兌換,這導致港幣大幅貶值,民眾悉數淪為破產者。但凡有抗拒不用軍票者,均會受到嚴刑對待:
在日本總督通令禁止使用港幣後,日軍便大肆搜查,一經發現居民依然藏有港幣而未兌換的,則施加酷刑,毒打、「灌水」(把污水或辣水灌入腹中,然後踏受灌者腹部,使水從口鼻噴出)、「老虎櫈」、「脫指甲」、「夾手指」、「放飛機」等,無奇不有,被施刑者往往因抵受不了痛苦而死亡。
至1945 年 8 月,軍票發行量高達 196 億日元。軍票泛濫,不只香港居民財產貶值破產,更加導致通貨膨脹失控,經濟崩潰,百業停頓。米、肉類、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價格飆升。如1945年米價高達90元一斤,花生油128元一斤;百物騰貴,漲價數倍乃至數十倍,遠超一般市民的承受能力。如有軍票者,還可以換取糧票,然後再憑票換米。然而,糧荒下每人一天最多只能換取六兩四錢大米,即約200克或一碗白飯的份量,是不可能讓人吃飽的。於是,市民面黃肌瘦,餓殍滿街,每天大批人餓死。小林英夫指出,社會出現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慘不忍睹景象:
街上到處都是死人屍體。搬運屍體的人一個抱着頭、一個提着腿, 然後再把屍體放到車上。即使是尚有一絲氣息的人也會被當作死人埋到坑裡。
在貧困生活中餓死的人增加,屍體被隨意擱置,甚至出現搶奪屍體爭相食用的悲慘境地。據說小孩子被隨意帶走殺害、販賣孩子肉的事件也時有發生。
據鮫島隆盛所見,飢餓迫使部分窮人捕食犬、貓、鼠類,甚至傳聞有人食人肉。街頭可見剔除老鼠毛髮者及被剝皮的嬰兒屍體,反映生存環境極度惡化。他描述了這樣的人間地獄:
天下再沒有比那些受軍隊淫威所欺凌的民眾更可憐的了……戰爭的恐怖、不安與暴虐仍然到處彌漫。——日漸面臨糧食、飲水、燃料、電力等生活必需物資的缺乏,因而民面有饑色,野有餓莩,街巷且常見有無人照顧的遺屍。當時,有一種叫做「屍體搬運車」的令人生懼的車箱,每日巡駛清理路上的屍體。路上的遺屍越來越多……兼以美軍飛機開始了頻繁的轟炸,每次突襲,總是死傷慘烈。
值得注意的,民眾慘受日軍逼害外,他們數年來也如鮫島所說的,一直承受來自盟軍空襲造成的二次、三次傷害,以至骨肉分離,朝不保夕。日軍投降前夕,整個香港早已是滿目瘡痍,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今天回首,仍不禁使人膽顫心驚。
直至1945年8月15日本投降,香港終於擺脫了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痛苦歲月。
以史為鑒:銘記歷史,珍愛和平
就在1941-1945年這「三年零八個月」的淪陷歲月中,值得自豪的就是──香港仍有一支勇敢的隊伍在抗敵護土。以新界居民為主力的港九獨立大隊(1943年年底併入中國共產黨廣東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成為香港境內的重要抗日武裝。東江縱隊在山區開展游擊戰,襲擊日軍據點,擾亂日人的運輸補給,以武力對抗巡邏日軍,懲戒漢奸,營救數十名外國人脫離險境。縱隊還未成立前的遊擊隊員還參與了「秘密大營救」的工作,於1942年冒險護送鄒韜奮、茅盾、何香凝、胡繩、胡愈之、于伶、柳亞子等八百名抗日文化人逃出日軍包圍圈。獲得他們救助的,還有1944 年被日軍擊落的美軍飛行員克爾,此舉不但呈現了香港民眾參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身影,還向日軍展示香港居民抵抗外敵的意志、勇氣與能力。
香港的抗戰歷史,留下了無數的傷痕與抗爭故事,這一切不僅保存於史料字縫間,同時也成為數代香港人的歷史記憶。三年零八個月的淪陷歲月,是香港歷史上最為黑暗的時期,也是銘刻在香港歷史深處的一道永難癒合的傷疤。藍塘道慘案、聖士提反書院大屠殺、日軍擅闖民居姦淫擄掠、大批無辜生命被放逐至荒島、滿街餓殍垂死掙扎……侵略者的罪行,已被一一記入史冊,也烙印於倖存者的口述史與回憶錄中,這一切都成為中國人抗戰歷史記憶的組成內容。
抗戰勝利紀念日,是召回歷史記憶的時刻,提醒我們民族曾經經歷的傷痛,讓新一代知道中國曾經受到何等的欺壓與傷害,從而了解國家的過去,認識當下的國家發展前景,培養出家國觀念與保持清醒的時局觀念,讓父祖輩曾經承受的苦痛不再延續,也從先烈的抗戰事蹟中承傳他們守土衛國的情志與愛國精神。
「和平」,從來都是得來不易的,它不是憑空而降的;無數人在實現和平的過程中受盡了磨難與苦痛,也有無數的先烈為此作出巨大的犧牲和貢獻。我們銘記歷史,不是為了延續仇恨,乃是為了延續和平的歲月,同時也要以史為鑒、自強不息,並且常存憂患意識,保持居安思危的清醒頭腦,齊心合力開創更美好的未來。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5年7-9月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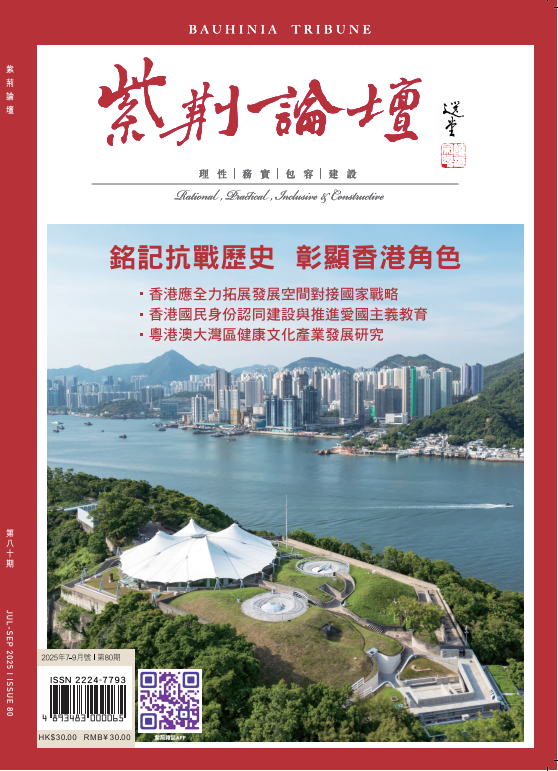







 今日熱搜
今日熱搜

 本週熱搜
本週熱搜

 本月熱搜
本月熱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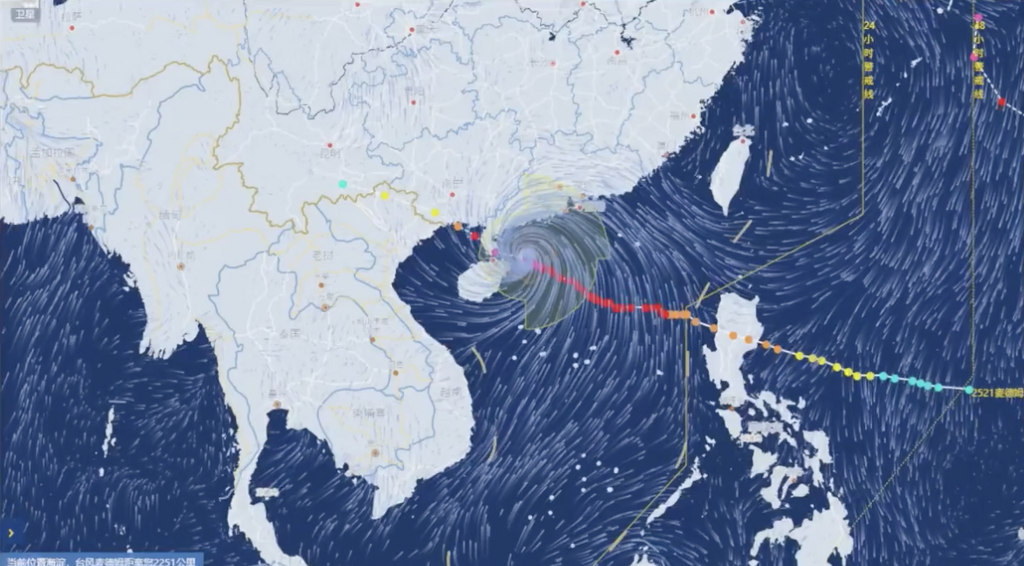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