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邢文威 | 亞太城鄉永續發展學人
2021年,香港特區政府提出建設「北部都會區」(北都),力求媲美以國際金融中心為標誌的維港都會區,成為引領香港創科發展的新引擎,形成「南金融、北創科」的全新經濟格局,以促進深港合作,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隨著北都建設進程的推進,此前少被提及的香港城鄉關係成為關注的焦點。
引言
香港的發展常被描述為「從小漁村變為國際都市」,但香港目前仍有近600個鄉村,其中北都範圍內就有234個認可鄉村。這也使得「城鄉共融」成為北都六大規劃原則的首位,願景之一便是營造「城市與鄉郊結合、發展與保育並存」的都會景觀。
香港鄉村發展面臨著城市化背景下的普遍困境。作為高度城市化地區,香港無城鄉戶籍之分,逾700萬人口中絕大多數生活在城市,但鄉村面積遠超城市,城市建成區僅約佔總土地面積的25%,廣闊疏落的鄉村地帶與高樓密集的城市地區相鄰。自上世紀60年代工業化興起後,農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或移居海外,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諸多偏遠鄉村淪為空心村,香港遭遇了全球城市化進程中常見的鄉村衰敗問題。
北都整合元朗、北區多個新市鎮、新發展區和發展樞紐及相鄰鄉郊地區,陸地面積約三萬公頃,佔香港總陸地面積的近27%。妥善解决鄉村發展困局、處理好城鄉關係,不僅對北都建設的順利推進至關重要,更關乎香港的長治久安和「一國兩制」的行穩致遠。
香港城鄉發展失衡的歷史脉絡與成因
(一)港九優先發展導向下的新界發展空窗
1842年開埠之前,香港還是清朝邊陲之地,受廣州府新安縣管轄,人口不足一萬,是典型的農業社會。香港開埠初期,被定位為英國在遠東的軍事基地、外貿交易站,經濟上以轉口貿易為主,實行「自由放任」「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政策,城市規劃重點在於香港島及九龍地區,建立了規劃制度和相應機構,維港兩岸逐漸發展成為商業中心,形成了以維多利亞港為中心、香港島與九龍半島為兩翼的城市格局,香港開始興起以自由貿易港為核心的工商業發展及城市建設模式。
1898年,英國租借新界99年。不同於香港島和九龍半島是永久「割讓地」,新界作為租借地,新界鄉村原居民對土地永久持有,在土地權益方面與「割讓地」不同。為了妥善處理新界原居民的合法權益,英國對新界並沒有進行深遠的改造,新界基本保持了農業社會的面貌。香港的城市與鄉村,出現治理體系、產業類型、基建發展的高度分化,香港人口也主要聚居在城市地區。有學者認為,英國租借新界的真正目的就在於窺準新界土地的升值潜力,英國人在新界的統治以政治經濟利益先行而不是注重社會文化實踐,在處理新界村民的固有價值和制度上,也限於以土地為主。
(二)城市化主導下新界鄉村的衰敗困局
香港與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一樣,同樣經歷了城市化過程中鄉村的衰敗。二戰之後,香港經濟結構的改變,導致從城市轉移出來的產業急於尋求新的發展空間。內地移民來港疊加嬰兒潮,人口由1945年約60萬急增至1965年360萬,同樣需要增闢空間解決房屋供應問題。1973年,港英政府出台新市鎮計劃,於1973至1987年間,分三階段在新界鄉郊發展九個新市鎮,將市區過於擁擠的人口和產業逐漸遷至新界。九個新市鎮面積超過160平方公里,佔新界土地面積達21%。到1996年,香港622萬人口中已有292萬人住在新界及離島,佔全港人口的47%。
在香港新市鎮進程中,推行的土地流轉制度,對擁有土地的原居民提供了經濟誘因,但也導致了鄉村農地棄耕、農業衰敗。在人口方面,城鄉產業結構、經濟收益的日漸懸殊,令鄉村居民投身於第二、三產業,鄉村人口大幅外流。而臨近城市建成區的鄉村,因交通便利、相對廉價的住房成本、吸引不少城市人口居住,其傳統的鄉村形態日漸被城市同化。
香港城鄉的互動關係,主要由城市化過程主導,鄉村衰敗與城市化相伴而生,加之未有完善的政策措施保障,偏遠鄉村未能吸引市場資本的投入,鄉村發展陷入政府、市場的雙重失靈,出現普遍的人口流失、產業不興的衰敗困局。
(三)歷史遺留政策對鄉村發展的深層制約
隨著香港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港英政府時期的諸多政策措施成為了歷史遺留問題。基於鄉村傳統的管治措施,與社會發展需要、現代法治觀念等產生衝突。特別是實施的一系列土地政策,在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方面,都存在較大的模糊空間。在隨後的鄉村發展中,土地問題成為核心的掣肘因素,衍生出棕地問題、祖堂地問題、丁屋問題等。這些都極大地限制了目前的鄉村發展,甚至造成香港社會發展的重要矛盾。因此,檢視歷史遺留的鄉村政策問題,破解發展阻礙,成為城鄉統籌發展階段的重要政策訴求。
因新界不同於香港島、九龍半島的租借地性質,以及港九地區快速的轉口港發展,新界延續了成熟的傳統農業社會面貌,鄉村發展未受到重視。港英政府租借新界之初,即遭到強烈反抗,更無意深入介入新界治理,並積極利用新界的宗族傳統、社會網絡,維護新界管治。對新界鄉村的管理,主要是以土地政策為核心,以行政手段將村民擁有的土地永業權改為承租權,挖掘新界土地價值,並以懷柔手段,安撫民眾情緒。在這一時期,港英政府的鄉村政策,主要基於傳統的鄉村功能,以建立土地管理制度、穩定管治為核心。
(四)鄉村發展系統性支持缺失與治理困境
香港1,100餘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只有約4平方公里用作耕種,700多萬人口中農業人口僅4,000餘人,第一產業整體農業人口比例和農業GDP佔比均低於0.1%,鄉村對香港社會經濟發展的直接貢獻較弱,常被政府忽視,也沒有全面的政策來促進鄉村發展和城鄉融合。
此外,不同於內地農村土地集體所有,香港鄉村的農地屬原居民私人所有。在香港進行鄉村建設時,不僅要面對眾多產權擁有者,往往還要面臨私人產權與集體利益的衝突,這不僅給集體行動帶來困境,而且阻礙了集體經濟的發展,也讓原居民缺少了經濟層面重要的維繫紐帶。基於城市場景而制定的經營政策和牌照發放政策,往往也不適用於鄉村場景。由於鄉村人口的外流,政府減少了對鄉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這些問題都讓原本已經衰敗的香港鄉村的振興之路更加艱難。
在治理層面,歷史上,香港一直缺乏系統的鄉村發展政策,相關政策在不同時期分散於土地、治理、產業、生態等方面。自香港回歸以來,雖已陸續開展對鄉村歷史遺留政策的檢視和政策創新。但是,針對某一具體政策範疇的單一檢視,並不能從整體上回應鄉村發展面臨的錯綜複雜的難題。
促進香港城鄉可持續發展的建議
前文梳理了由1842年至今香港城鄉變遷的主要發展脉絡,香港鄉村經歷了城市化過程中的普遍衰敗,並在可持續發展熱潮中,以城鄉共融探索復興之路。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鄉村功能不再僅局限於向城市輸出人口、土地等發展資源,深刻認識當代鄉村多元價值,成為妥善處理城鄉關係的必要前提。圍繞改善城鄉關係、推動鄉村發展,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相繼開展探索鄉村振興,積極回應現代化進程中的鄉村問題。
(一)構建綜合系統的鄉村發展政策體系
香港鄉村發展面臨的問題具有複合型特徵,既包含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普遍存在的鄉村衰敗現象,也存在因特殊歷史背景形成的獨特挑戰。自回歸以來,特區政府雖對部分歷史遺留政策進行了檢視與調整,但單一領域的政策優化難以應對鄉村發展的複雜局面。當前,香港土地房屋問題突出、社會貧富差距顯著、城鄉矛盾時有顯現,亟需將鄉村發展納入整體發展戰略,構建系統性政策框架。
建議成立跨部門的「鄉村發展統籌委員會」,由政務司司長牽頭,整合發展局、地政總署、民政事務總署、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等部門資源,制定香港鄉村振興戰略規劃。該規劃應明確鄉村在香港可持續發展中的戰略定位,劃定生態保護、產業發展、文化傳承等功能分區,建立「政府引導、市場參與、社區主導」的多元協作機制。同時,設立「鄉村發展專項基金」,重點支持土地整理、基礎設施改善和產業培育項目,並通過政策創新吸引社會資本投入鄉村建設。此外,應系統梳理現有鄉村政策,消除政策壁壘,借鑒內地鄉村振興經驗及國際鄉村發展案例,結合香港實際進行本土化改造,形成覆蓋土地、產業、文化、治理等多領域的政策合力。
(二)破解歷史遺留問題,疏通鄉村發展梗阻
歷史遺留的土地問題是制約香港鄉村發展的核心障礙,其中棕地利用混亂、祖堂地管理不規範、丁屋政策與現代規劃脫節等問題尤為突出。這些問題涉及複雜的利益關係,處理不當易引發社會矛盾,需以審慎態度推進改革。
針對棕地問題,應建立「分類整治、多元利用」機制,對污染嚴重、效益低下的棕地實施生態修復,對區位優越的棕地通過「土地共享計劃」整合開發,確保原土地權益人參與開發收益分配。對於祖堂地,需修訂相關法律,明確祖堂地權屬登記規則,規範司理的管理權限與責任,建立祖堂地流轉交易平台,在保障宗族合法權益的前提下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關於丁屋政策,應在尊重原居民傳統權益的基礎上,完善申請資格審核機制,鼓勵集中建設新型丁屋社區,配套公共服務設施,避免零星建設造成的資源浪費。
同時,針對空心村和偏遠鄉村的發展困境,需實施「精準扶持」政策。對人口流失嚴重的空心村,可通過「村屋活化計劃」改造閒置房屋,發展鄉村民宿、創意工作室等業態;對基建落後的偏遠鄉村,優先完善交通接駁系統,建設小型污水處理設施、社區服務中心等基礎配套,打破「發展滯後—資源匱乏」的惡性循環,激活其作為城市人口疏解空間的潜力。
(三)推動城鄉融合發展,拓展可持續發展空間
新界鄉村地帶是香港未來發展的重要戰略空間,北都建設為城鄉融合提供了歷史性機遇。應總結新市鎮發展的經驗教訓,避免重蹈「城市擴張—鄉村衰敗」的覆轍,構建城鄉功能互補、協同發展的新格局。
在空間規劃上,建立「城市核心區—鄉村轉型區—生態保育區」的梯度發展模式,明確各區域的開發強度與保護要求。加強城鄉交通網絡銜接,規劃建設連接新界鄉村與都會區的快速公交系統,縮短時空距離。在產業協同方面,依託北都的科創產業優勢,在周邊鄉村培育科技農業、創意設計、鄉村旅遊等特色產業,形成「城市研發+鄉村轉化」的產業鏈條。
完善城鄉要素流動機制,允許城市資本有序進入鄉村投資符合規劃的產業項目,同時保障原居民在土地增值中的合理收益。建立「城鄉發展基金」,從城市開發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反哺鄉村建設,用於改善鄉村公共服務。通過制度創新,使鄉村地區既能為城市發展提供拓展空間,又能借助城市資源實現自身振興,形成城鄉互利共贏的發展格局。
(四)珍視鄉土文化價值,增強身份認同與社會凝聚力
鄉村是中華傳統文化在香港傳承和發展的重要載體,承載著獨特的歷史記憶與文化基因,對增強市民尤其是青年一代的身份認同具有重要意義。保護和活化鄉村文化資源,是鄉村振興的應有之義。
建議開展鄉村文化資源普查,建立「香港鄉村文化遺產名錄」,對傳統村落、歷史建築、民俗活動等進行系統保護。支持太平清醮、林村許願節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創新,結合現代藝術形式開發文創產品,提升文化影響力。修復抗戰歷史遺跡,挖掘其背後的愛國愛港愛鄉故事,將其打造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建議推動鄉村文化體驗與旅遊融合發展,規劃「香港鄉村文化走廊」,串聯特色村落、民俗景點和自然景觀,開發研學旅行、文化體驗等旅遊綫路。在學校教育中增加香港鄉村歷史文化內容,組織青少年參與鄉村志願服務、農耕體驗等活動,增強對本土文化的認知與認同。通過文化賦能,使鄉村成為傳承中華文脉、凝聚社會共識的精神家園。
結語:以城鄉共融踐行可持續發展理念
北都的建設,標誌著香港進入新一輪新界城市化進程。作為香港最具潜力的發展空間,這一進程必然圍繞鄉村地帶展開,其核心挑戰在於如何落實「城鄉共融」原則——既要規避歷史上新市鎮發展導致的「城興村衰」教訓,破解發展與保護的長期爭議,更要超越傳統城鄉二元思維,讓鄉村的歷史、文化、生態多元價值與城市功能形成互補互動。
實現這一願景,需以系統性政策為支撑,制定全域性、前瞻性的鄉村發展戰略,整合土地、文化、治理等多領域政策,破解棕地、祖堂地、丁屋等歷史遺留問題,通過「利益共享」機制平衡各方權益;需借鑒內地鄉村振興與國際鄉村發展經驗,結合香港實際,構建「政府引導—市場參與—社區主導」的協同機制,促進城鄉要素雙向流動;更要將鄉村發展納入香港整體可持續發展框架,讓北都真正成為匯聚科技與文化、串連歷史與現代的典範。
從根本而言,香港鄉村振興絕非局部地區的單點改善,而是關乎「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社會長治久安的戰略舉措。唯有珍視鄉村價值、激活鄉村活力,才能拓展發展新空間、緩解社會矛盾,讓城市與鄉村在共生共榮中,為香港沉澱更深厚的人文精神打造更良好的生態環境,築牢可持續發展的根基。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5年7-9月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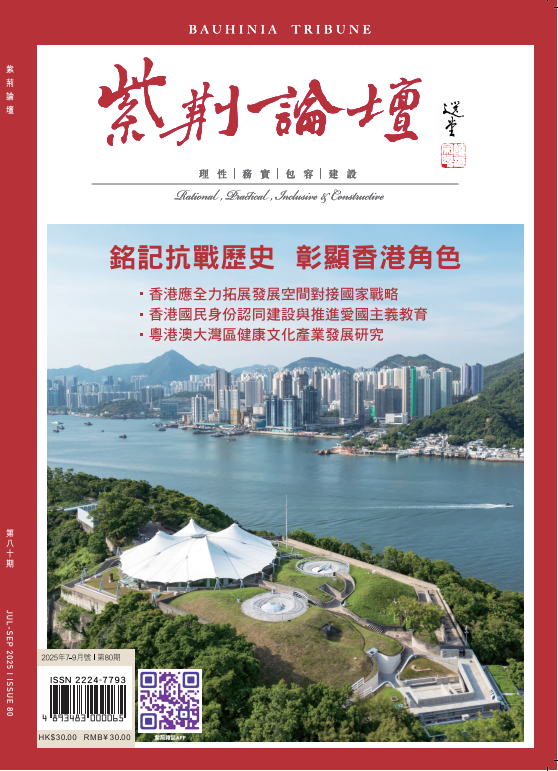







 今日熱搜
今日熱搜

 本週熱搜
本週熱搜

 本月熱搜
本月熱搜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