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王慧娟 | 紫荊雜誌社主任編輯
2025年,世界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香港和澳門這兩顆曾被殖民國家侵佔的東方明珠,正以「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的全新政治身份,重新書寫與祖國的關係史。這段80年的歷程不僅是對戰爭的反思,更為現代國家治理與共同體認同構建提供了深層啟示。
被侵佔的雙重性與空間政治的矛盾性
回顧歷史,香港先後經《南京條約》(1842年)、《北京條約》(1860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1898年)被逐步割讓;澳門則自明代租借地演變為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下的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門」,在帝國邊緣形成西方法權管轄的侵佔地。這類空間具有鮮明的雙重性:一方面,英國在香港推行「華洋分治」(如1888年的《山頂區保留條例》),葡萄牙在澳門確立「葡人治澳」體制,以種族隔離和法律區隔構築殖民秩序;另一方面,兩地又成為文明交互樞紐——香港維多利亞港一度承擔著中國半數的對外貿易,澳門議事亭前地既矗立著葡國總督雕像,也是華人「茶話會」議政之所,權力符號與跨文化實踐在此共生。
具有殖民性質統治香港的核心策略是「去主體化」和「去國家化」。英國在香港實行「沒有代表的治理」,直至1985年才設立首個非官守議員佔多數的立法局;葡萄牙在澳門長期推行葡萄牙化政策,禁止華人學習中文法律,甚至試圖消滅中國傳統文化。殖民代議制的虛置(香港)與文化同化的企圖(澳門),終究未能根除華人的文化根基。正如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言,霸權的維持不僅依靠強制,更依賴文化認同的建構。殖民當局的文化霸權在抗戰烽火中遭遇了根本性挑戰:1941年香港保衛戰,由600名香港華人組成的「香港華人軍」(又稱「香港華人集團軍」)在黃泥湧峽與日軍血戰,他們身著英軍制服,臂章上卻繡著「保家衛國」的中文標語;1942年,澳門鏡湖醫院藉「中立區」之便,救治傷員、培訓醫護人員、秘密轉運物資,支援中山遊擊戰。這些行動表明,當民族危機超越殖民邊界時,華人居民的身份認同便衝破了殖民當局設定的屬地公民框架,回歸到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明母體之中,也為後殖民時代的「去殖化」——如香港更換步操、澳門強化愛國教育——留下歷史根脈。

從被動包容到主動建構的民族身份覺醒
戰爭的殘酷,反而促使港澳華人社會超越殖民邊界,自發形成民族與文明的「想像共同體」。抗日戰爭是一場民族與文明的保衛戰,它迫使港澳居民在殖民國家侵佔地居民與「中國公民」的雙重身份中作出抉擇。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香港各界踴躍發起救助活動,形式多樣:上流社會舉辦各類餐會、舞會、賽馬會為難民籌款,基層民眾則以賣花、街頭義演、逐戶募捐等形式籌款。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香港學生賑濟會透過街頭賣花、賣物會、義唱、義演、節食活動等方式,共募集兩萬餘港元。1938年10月,香港同胞將慶祝「雙十節」的宴會款項改作捐募寒衣,76個商團聯合募集寒衣36萬件;1941年8月,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在香港發起「一碗飯運動」。
最具象徵意義的是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的成立。1942年,百餘名香港青年突破英軍防線,加入東江縱隊,組建了香港本土第一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隊伍。他們在港九新界建立了20多個情報站,營救了800多名滯港文化名人(包括茅盾、鄒韜奮、胡風等),並突襲日軍啟德機場,炸毀6架戰機。隊伍成員來自不同階層——英資洋行打字員、香港大學學生、九龍城寨碼頭工人......他們以「中國共產黨黨員」「中華民族抗日戰士」為共同身份,殖民統治下的身份碎片化在民族危亡之際被整合為國家主體性——戰爭成為重構政治與身份認同的熔爐。
「澳門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簡稱「澳門四界救災會」)是抗戰時期澳門最重要的愛國團體之一。1937年8月成立後,該會除籌款賑災外,更把後期核心工作轉向組織青年回國服務團,深入廣東抗日前線開展戰地服務。先後有11批青年以血肉之軀,踐行了「共拯我被難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的宗旨。不僅填補了廣東前線後勤與團員缺口,更以14人的犧牲詮釋了澳門同胞與祖國同生共死的民族氣節。這段歷史也凸顯了澳門在抗日戰爭中的特殊地位:不是「中立孤島」,而是愛國熱血匯流之地。
港澳同胞的抗戰行動撕破了殖民國家當局「中立」「非政治化」的偽裝,展現了華人社會自發的民族與文明共同體意識。正如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中指出的,當人們通過共同的苦難、共同的抗爭、共同的記憶形成「想象的聯結」,國家認同便超越了地理邊界與政治制度區隔。
在殖民國家侵佔秩序的裂縫處,港澳形成了「地方」與「中央」的隱性聯動。表面上,葡萄牙政府在二戰中宣布「中立」,然而澳門實則成為華南地區的抗戰補給站。1943年,澳門商人何賢透過大豐銀號將澳門博彩收益的40%(約500萬澳門元)兌換成黃金,經澳門內港運往重慶;1944年,中共地下黨在澳門鏡湖醫院設立秘密交通站,利用澳門的葡萄牙郵電系統向延安發送了1,200多份日軍華南部署情報。這些行動之所以能夠實現,正是因為殖民國家當局在商業利益與政治投機之間選擇了實用主義:既不敢得罪日軍(1940年日軍曾在澳門邊界陳兵三萬施壓),也不願切斷與中國內地的經濟聯繫。這種「騎牆姿態」客觀上為華人社會的抗日活動留下縫隙,使港澳成為殖民主權與國家主權博弈的「灰色地帶」,而華人社會則在這種博弈中主動建構了與內地的隱性政治聯動。
「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的現實根基
(一)殖民治理與「去國家化」的破產。二戰結束後,港澳並未迎來去殖民化的曙光。英國以「保衛香港」為由拒絕歸還新界,葡萄牙則將澳門視為「海外省」。冷戰格局下,兩地殖民國家當局轉而推行「去政治化的政治」:香港以「東方之珠」經濟神話和消費主義淡化政治認同;澳門則以「博彩旅遊」的產業定位和文化、產業多元化來包裝殖民本質。此種治理策略導致部分港澳居民形成經濟自由主義與政治虛無主義的混合心態——一些人甚至在2019年「修例風波」中,將殖民時代的港英政府奉為理想的治理模式典範,暴露出殖民化所遺留下的深層認同異化。
然而抗戰記憶正成為破解這一異化的關鍵鑰匙。2021年,香港特區政府將「國家安全教育日」納入中小學課程;港澳特區政府和民間團體也多次以研討會、藝術表演、觀影展覽等形式普及抗戰歷史、開展相關學習活動,加強國家安全教育及對東江縱隊、澳門難民潮賑濟史實等的宣傳,解構殖民敘事。當港澳居民認識到在民族危亡之際,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保護了他們的祖輩,是全國各族人民群眾與海外華人同舟共濟,擔負保衛家園的歷史使命時,「去國家化」的神話便不攻自破。
(二)愛國者治港治澳的三重邏輯。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落實「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原則。這是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和長治久安、推動港澳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新的更大貢獻的有力保障。這一原則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必然性與理論正當性。
首先在主權層面,港澳先後完成由殖民國家當局侵佔地區向中國主權下的特別行政區的歷史性轉變。被侵佔時期的慘痛教訓印證了主權、管治權對民生福祉的決定性意義。1941年香港淪陷後,日軍以1:4的比率強制兌換軍票(黑市實際貶值至1:10),令70%以上的華人陷入赤貧;1943年澳門因日軍封鎖而饑荒蔓延,米價暴漲167倍,約4萬居民(佔當時澳門人口的10%)死亡。這些災難的根源在於殖民政權無力維護屬地安全與發展權益,唯有回歸國家主權框架,依託「一國兩制」制度優勢,港澳居民的生存權與發展權才能獲得堅實保障。「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原則通過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統一,徹底終結外部勢力干預的可能性,確保港澳治理始終服務於國家與民族整體利益。
從共同體角度看,港澳實現了從表層地域認同到深層文明自覺的轉變。抗戰時期港澳華人的行動表明,中華文明共同體意識具有強大凝聚力,其根基不僅在於共同的語言、文化、歷史經驗,更在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政治倫理。香港國安法規定「行政長官、主要官員、立法會議員、司法官員必須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這並非對「兩制」的限制,而是通過法律將管治者責任錨定於「一國」根基,並確認「港澳的命運始終與國家興衰緊密相連」的現實邏輯,這既是中華文明「以文化心、以天下為己任」治理傳統的當代延續,也是對歷史規律的現實確認。
從治理邏輯看,港澳實現了從被侵佔霸凌向愛國者協商治理的轉型。殖民統治的本質是排他性霸權,而「一國兩制」的核心是包容性治理。被殖民國家侵佔時期的所謂「協商」實為一種生存策略。抗戰時期,港澳華人社會透過「抗日聯合會」「救災會」等民間組織實現跨階層、跨行業協商合作,為今日制度設計提供了歷史借鑒。今天的「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原則將這種協商傳統提升到制度層面:改革後的香港立法會90個議席由直選(20席)、功能界別(30席)、選舉委員會(40席)三方面構成;澳門立法會則包括直選(14席)、間選(12席)、委任(7席)。這些設計衝破了殖民時期的種族壁壘,確保分處不同界別、持不同意見的人士能在「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的前提下參與治理。由此,港澳在維護國家主權的同時,通過制度化差異協商實現了多元一體的包容性治理,彰顯了中國政治文明的獨特智慧。
在「國家」與「地方」的辯證中走向未來
回顧港澳抗戰史不難發現,一條清晰的政治命題貫穿始終:當「地方」遭遇外來壓迫,「國家」便是最堅實的後盾;當「國家」面臨生存危機,「地方」亦是不可分割的血肉,這種國家與地方之間的辯證關係,在「一國兩制」的當代實踐中獲得了新的時代內涵。
對香港而言,「愛國者治港」並非對「兩制」的收縮,而是對「一國」的強化。唯有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香港才能繼續保持「超級聯繫人」地位,才能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展現「國家所需、香港所長」。
對澳門而言,從博彩單一經濟走向粵港澳大灣區中心城市的轉型,本質上是從殖民遺留的依賴模式邁向國家戰略的深度融合。抗戰時期,澳門華人通過支援祖國完成身份覺醒;今天的澳門則通過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葡平台建設,成為國家對外交往合作的重要窗口。更深刻的啟示在於,港澳的變遷顛覆了西方政治學中國家與社會對立、主權與自治矛盾的理論範式。在這裡,「一國」不是抽象的法律概念,而是承載著五千年文明記憶的共同體;「兩制」亦非制度對抗的產物,而是中華文明「和而不同」智慧的當代實踐。
在抗戰勝利80周年之際重思港澳政治哲學,實際上是在回答一個更宏大的問題:在全球化時代應該如何構建既有民族根脈、又具世界視野的現代國家治理模式?從「殖民國家侵佔地」到「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改變的是治理主體與制度形態,不變的是國家至上、民族為先的核心價值,是血濃於水、休戚與共的共同體精神。
愛國從來不是地理歸屬,而是一種文明自覺;治理港澳也從來不是權力遊戲,而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必然。站在新的歷史起點,港澳需要把抗戰記憶轉化為建設國家的澎湃動力,「讓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不僅成為制度原則,更成為全體居民的文化自覺。唯有如此,這兩顆曾被割裂的東方之珠,才能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綻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5年7-9月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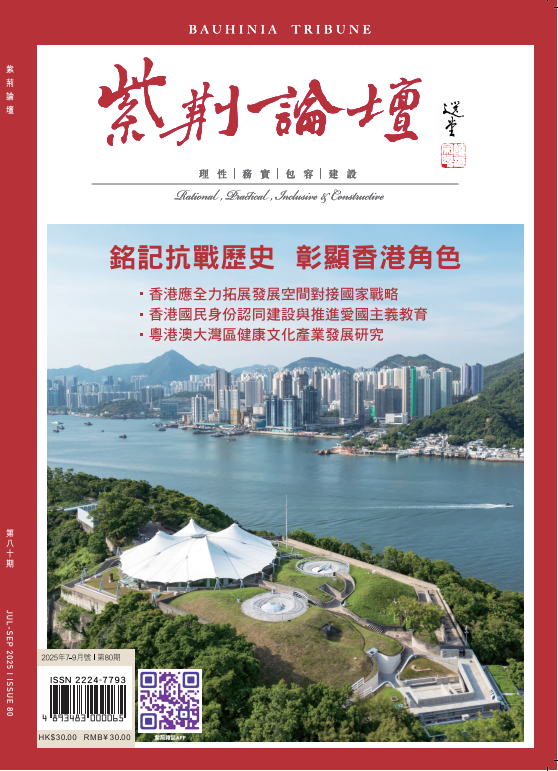







 今日熱搜
今日熱搜

 本週熱搜
本週熱搜

 本月熱搜
本月熱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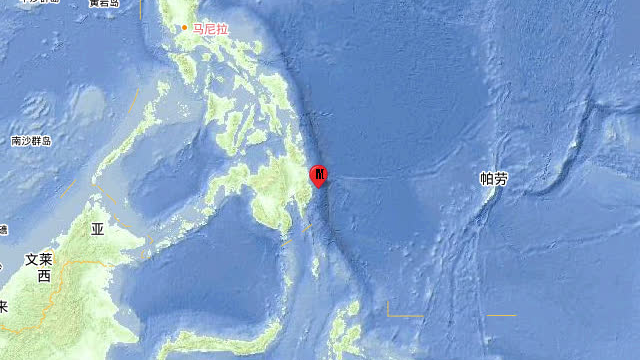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