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朱家健
近日,接二連三揭發有獨居長者在家中離逝,死者被發現時已仙遊多時,也有個案指個別死者已失蹤逾一年,情況令人關注。香港作為一個現代化的城市,發生這種悲劇實屬不幸。先不碰及死者的死因是病故、失救還是其他,死者陳屍多天未有人及時發現,已見證社會的涼薄,鄰居未有聞到異味,更未有察覺到獨居長者未有外出購買餸菜、點外賣食物或丟棄垃圾,管理員也沒有發覺異常,而死者的親人也不聞不問,即使未有到訪,甚至也沒有以電話或短訊聯絡,也不覺事有蹊蹺,即使是查看死者信箱、水電費單、屋租和管理費處於未繳交狀況,也未有任何人跟進,真是世態炎涼。
個別獨居長者有的老伴子女已離開,個別的子女更已移民,較為健談的長者或會飲茶、聯誼、下棋或參與社交活動,個別孤癖的長者未必有朋友或其他人主動聯絡,生活枯燥寂寞,甚至未有人發現他們突然在生活中的淡出,他們未必需要社區財政或醫療資源的援助,但他們絕對是社福資源網需要涵蓋的一群,不應該被遺忘。社福機構或只會盤算每年有多少撥款、多少次的公開籌款、總幹事的薪津,然後再在“會員名單”(即受助對象)提供恆常服務;然而,在名單內的長者通常是較主動、較活躍又最吸引注意力的一群,不在大部分社福機構服務名單內的長者,倒過來可能就是長期被忽略,反而需要關心、注意或投放社福資源的零星個體,這個組群的長者未必對排隊領取福袋或飯盒有興趣,也未必踴躍參與社區聯誼活動,但總不能未見他們影縱,便單向武斷地推測他們不在香港境內或到被子女接回家生活。
在大數據年內,其實無論是水電煤賬單、管理費、公屋租金、樂悠卡、八達通消費、出入境紀錄,手提電話和數據使用量、醫院覆診紀錄、銀行戶口結餘,均能以人工智能推敲個別人士是否屬高危失蹤人士的可能性,社署可以再分急緩次序去派員跟進個案。區議員和關愛隊(但也不宜獲發數千元車馬費)也可主動關心區內來自私樓家庭和公屋家庭的長者,尤其是較內向、身體有殘疾隱病、喪偶和獨居的長者,在條件和長者同意下,可以安排定期家訪和電話問好,也是地區保長的份內事;管理員也可以透過管理公司主動向業主或租客聯絡;鄰居之間也可以多發揮鄰里守望相助的精神,多串門、多關懷、多溝通,主動關心身邊的長者家庭;子女也應主動關心不同住的父母或旁系親屬長輩,不時瞭解他們的行蹤和病歷。
社署的角色,除了是外判服務和監督,更可以是主動去做服務,例如平時外判社福機構較少接觸、不屬於受助對象範圍,或較偏遠、更麻煩的個案對象,既能控制成本,減少撥款,也能把服務接觸到獨居長者等優先而容易被忽略的社會弱勢群體。
(作者係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副秘書長,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今日熱搜
今日熱搜

 本週熱搜
本週熱搜

 本月熱搜
本月熱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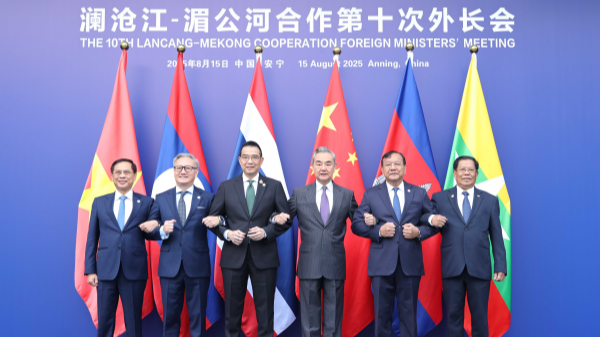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