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記者 黎知明 王慧娟
在香港立法會的議事廳與大大小小的政策研討現場,葉劉淑儀的身影始終與這座城市的公共事務緊密相連。從1975年赴倫敦考取港英政府職位,到如今深耕議會十七載,近五十年的時光裡,她從未涉足商界,也未擔任過企業獨立董事,正如她所言:“我一輩子幹的活就只是政府事務,還有就是議會事務,用英語來講就是government and politics。沒有從商,也沒有當什麼獨董,因為沒時間也沒能力。”這份對公共事務的專注與堅守,勾勒出她服務香港的清晰軌跡,也沉澱出她對這座城市發展的深刻思考。
生涯:從紀律部隊到議會,扎根公共事務

1975年,葉劉淑儀在倫敦通過考試,加入當時的港英政府,自此開啟了她與香港公共事務的半生羈絆。在她的職業生涯中,兩段經歷被視為關鍵節點——成為入境事務處處長,繼而擔任保安局長,七年的紀律部隊首長生涯,讓她對香港的治理體系有了更務實的認知。“對我影響最大當然是,第一成為入境事務處的處長,然後成為保安局長,當了七年紀律部隊的首長。”這段經歷不僅錘煉了她的執行力,更讓她懂得如何在政策推行中平衡公共利益與市民需求。
回歸初期,香港處於轉型適應階段,作為政府核心部門的負責人,她始終站在政策執行的一線。彼時的她,個性率直,有時會“衝口而出”,但這份坦誠也讓她更直接地傾聽市民的聲音。直到後來,她才逐漸意識到表達方式的重要性,“這幾年我覺得進步了很多。近年來已經比較少受到批評說講錯話了”,這種轉變並非妥協,而是源於對“如何讓政策被更多人理解”的深入思考。這也是她後來服務議會、連接政府與市民的重要基石。
2008年,葉劉淑儀當選香港立法會議員,此後便再也沒有離開過這個崗位,至今已十七載。從政府官員到議會代表,身份的轉變讓她的工作重心從“執行政策”轉向“監督與建言”,但不變的是與市民的緊密聯結。她深知議會工作的核心在於“接地氣”,正如她所說:“(立法會)選舉會拖著你跟市民互動,你一定要下去,經常要搞一些群眾的活動,還要接受市民的投訴,傾聽市民的要求。你不可能離地,雖然辛苦一點,但對於向特區政府提供政策意見是很有用的。”這種“不脫離市民”的工作方式,讓她的建言總能貼合香港的實際需求。
轉折:挫敗中的沉澱,斯坦福再出發
2003年,香港特區政府首次推動基本法第23條立法,由於諸多因素的干擾和阻撓,立法未能成功,這是葉劉淑儀職業生涯中最深刻的挫敗,卻也成為她人生轉折的契機。對此,有聲音表示當年是否“倉促上陣”,她明確回應:“當然不是倉促上陣,最理想來講,應該一回歸就立法,這是憲制的要求,但是時間不夠。最好是還沒有回歸時,拿出草案交給臨時立法會立法,這是最合適的時機。”她同時坦言,當時推動立法時有批評“為什麼只有一個女人去,沒有團隊,沒有其他司局長”,這也讓她看到團隊協作的重要性,“後來國安法立法,就非常重視團隊協作的精神”。
“這是個很大的挫敗,但也可以說成就了我後來的發展。因為我覺得要自己靜下來想一想,為什麼工作做得不夠好?”正是這份反思的勇氣,讓她決定暫時放下工作,前往美國深造。選擇斯坦福大學並非偶然,早在上世紀80年代,港英政府就曾派她到斯坦福攻讀商學院課程,“當時那個商學院的課程對我來講,我的數學基礎不好是很吃力的”,但這段經歷也讓她記住了這所校園優美、學術氛圍濃厚的大學,更讓她渴望有機會深入探索自己未曾觸及的領域。2003年,她再次踏入斯坦福,攻讀東亞研究,“三年念了很多書,經濟、政治、電影、文化等都念了。還學了日語,雖然現在日語完全忘了”。
在斯坦福的時光,是她的“充電期”。她不僅研究西方政治理論與民主制度的實踐案例,更補上了過去因忙碌而錯過的“國學課”,如《紅樓夢》及先秦文化,這都是在斯坦福與美國教授一同研讀的。“西方對我國古代的文化其實也有很深刻的研究”,這種跨文化的視角,讓她對中西方的差異與共通點有了更包容的理解。
更重要的是,在斯坦福,她敏銳地捕捉到科技發展的浪潮。“我在斯坦福領略一點非常重要,就是科技的重要性,見證了美國發達的科技產業。斯坦福大學的學生們已經在用Facebook了,當時谷歌、蘋果也都在使用了。”這段經歷埋下了她後來關注香港科技產業的種子,也讓她意識到“僅靠市場推動政策”的局限性。這一認知,成為她回港後推動科技政策的核心思路。
2003年,某位關心香港的高層人士一句話點醒了她:“你要注意修辭,注意你表達的方式,你的用心是好的,但是怎麼使市民聽得明白、獲得支持是需要技巧的。”這句話讓她更加重視“溝通的藝術”,也為她後來以更平和、客觀的態度參與政策辯論埋下伏筆。就在不久前立法會關於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的辯論中,儘管有關條例最終沒有通過,而作為條例支持者的她始終“儘量客觀,不情緒化”地解釋法理,其發言也獲得了一些年輕人的認同。這份轉變,正是源於挫敗後的沉澱與學習。
建言:為香港謀發展,深耕科技與公務員改革
從斯坦福回港後,葉劉淑儀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便是創辦匯賢智庫。這份事業的起步,離不開老同事的支持:“我都是靠我入境處的老同事幫忙,幫我找寫字樓,還加入當我的義工,目前還有很多入境處以及退休警務人員做義工,還有一些政務官也非常支持”,提及這些支持,她始終心懷感激,“我對於這些老同事的支持真的是非常感動,要感謝他們”。
匯賢智庫成為她推動政策研究的平台。她自掏腰包,組織國際科技學術團隊,撰寫了《創新政策與自由放任的局限性——比較視角下的香港政策》(Innovation Policy and the Limits of Laissez-faire-Hong Kong's Polic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一書,直指香港“完全靠市場進行推動的政策”的不足。然而,這本書並未得到特區政府的重視,“當時我交給特區政府,官員完全沒有興趣。我透過很多管道找到當時的財政司長,收了這本書,跟我拍了一張照,後來也完全沒有跟進”。
在她看來,香港科技產業的滯後,根源在於港英時代“自由放任經濟主義”的延續——“過去港英年代是自由經濟,當然也有政治的背景,因為只是一個短期的管理,為什麼要投放國之重器,不可能放在香港啊,所以自由放任的經濟主義非常適合香港。剛回歸時我們的官員還是承襲了這種思想”,這導致香港的科技發展“晚了20年”,“所以現在搞‘北都’不容易啊,投放要大得多,時間也要長得多”。
因此,當最新一份《施政報告》將“北都發展”列為核心時,她深感認同,並提出了三點建議:第一,北都發展必須 “破局”,“肯定要用破局的手法打破過去的很多程式定勢,要不然20年都幹不好”;第二,重視人工智能,“應該從公務員開始”,比如用人工智能取代翻譯及基礎文書等工作,“提升效率”,她認為“政府用人工智能工具其實比私人機構還晚,所以特首提出這個要用‘AI效能提升組’很重要”;第三,推動公務員改革,核心是“加強責任感”,“就是這個責任不要推,負責執行的部門要增加責任感”。
對於公務員體系中可能存在的“多做多錯,不做不錯”心態,她有著清醒的認知:“部門首長責任制是加強責任感。不光是不要出錯,如果你的部門辦事程式冗長,一年也批不出一個牌照,長期受人投訴,一直沒有提出改善建議,就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表現。所以不是不出錯這麼簡單,而是每個人都要積極作為。”這份對“責任”的強調,正是她對香港治理效率提升的核心期待。
育人:心繫青年未來,拓展多元成長路徑

在推動政策的同時,葉劉淑儀始終關注青年工作,她深知香港的未來在於青年。她在早年發起 “張騫計劃”,鼓勵香港年輕人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習,後來,隨著政府加大對青年海外及內地實習的投入,她便果斷調整方向,“改推其他議題,不斷與時並進”。如今,她的青年工作聚焦於“提供多元路徑”:對於喜歡政策研究的年輕人,她會親自帶領,幫助他們建立對公共事務的認知;對於有意從政的青年,她會告知從政有很多方面,如果參加選舉,她坦誠表示,“選舉不是每個人都適合的一杯茶”。她會引導他們關注政府的其他工作,如“諮詢、環保、甚至上訴性質的工作,政府在很多範疇上都有上訴機制”。
她還特別關注“國際關係”領域的青年培養。香港的優秀學生大多選擇醫科、法律或公務員,因為收入很高,“很少年輕人去念國際關係或公共政策”,但如今這一情況正在改變。她認為,年輕人多了機會去內地交流,更多地認識了國家的發展,而同時也要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國際關係人才,“將來應該要培養多一點這樣的人才”。
此外,她還帶領智庫研究“太空經濟”,即便知道不少老百姓會覺得“離地”,她仍堅持普及相關認知:“所有太空經濟都是靠衛星,我們有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在很多方面,可以利用太空經濟為內地的航天企業服務。”她希望通過這類前沿議題,拓寬青年的視野,讓他們看到香港在國家戰略中的獨特角色。
視野:立足變局,香港的定位與擔當
當下,中國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葉劉淑儀對香港的定位有著清晰的判斷。她認為,中國的崛起“是其他國家用什麼手段都不可能壓下去的,我們有國家的決心、領導人的決心、民族的素質,還有這麼龐大的資源”,而香港的優勢,不在於經濟總量或增長率,“不可能比得上內地的城市,因為地方小人口有限”,而在於“法治特別是普通法,還有金融和專業服務,這是非常重要的基石”,還有個優勢就是“國際化的環境”。
她表示,香港跟西方、跟東南亞的交流都非常廣泛。這種優勢,既是港英時代積累的遺產,也是香港未來發展的核心競爭力。但她也強調,香港的國際化不能再局限於西方,“過去港英時代主要是跟西方,把我們當做西方陣營的一份子”,而現在,“我們要拓展跟中東、南美、東南亞的聯繫,要加強跟全球南方的聯繫”。
對於中美關係的變化,她有著親身感受。2003-2006年在斯坦福時,“當時應該是中美關係的黃金年代”,美國老百姓享受著中國出口的價廉物美的產品,“加州自己房子裝修用的工具都是中國來的”;但到了2013-2014年後,隨著美國“重返亞洲”,中美關係逐漸轉向,“美國開始冒出很多的理論,諸如‘中國有百年大計要取代美國’‘中美之間難逃一戰’等”。對於美國發動關稅戰的影響,葉劉淑儀表示,按照經濟理論來講,美國這樣的經濟政策長期持續下去是會失敗的。目前對香港影響不大,主要因為香港有國家的庇護,在關稅戰中,中國是唯一有資格與美國談判的國家,因為現在的中國有實力了。當前的國際格局已經不是講理論,而是回到19世紀的說法“實力政治”(Realpolitik)。
結語:半生篤行,與香港共前行
近五十年的公共服務生涯,葉劉淑儀歷經香港的風雨變遷——從港英時代到回歸祖國,從紀律部隊首長到立法會議員,從政策執行者到青年引路人。她曾遭遇挫敗,卻在沉澱後重新出發;她始終扎根於市民之中,讓建言貼合香港實際;她心繫青年,為他們拓展成長路徑;她立足變局,清晰把握香港的定位與擔當。
正如她所說,當年的挫敗“成就了我後來的發展”,而香港的每一次挑戰,也都在成為這座城市前行的契機。如今,她仍在議會與政策研究的一線忙碌,用自己的經驗與智慧,為香港的發展建言獻策。這份“一生一事”的堅守,不僅是她個人的人生寫照,更折射出一代香港人為這座城市付出的努力——而這份努力,並在為香港的未來注入源源不斷的力量。
(本文發布於《紫荆》雜誌2025年10月號)







 今日熱搜
今日熱搜

 本週熱搜
本週熱搜

 本月熱搜
本月熱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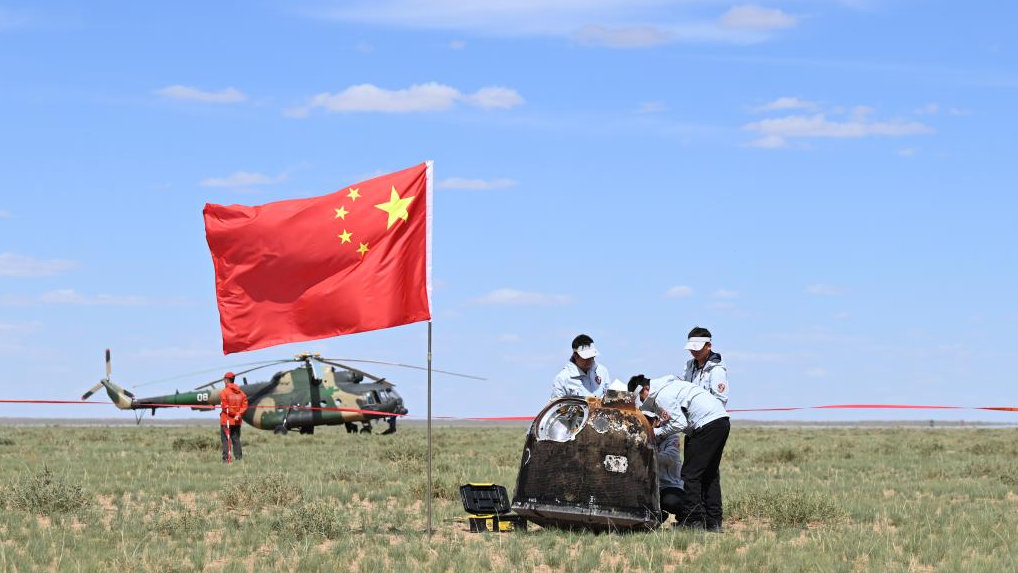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