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郭正林 |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教授、深圳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深北莫深港融合發展研究中心首席專家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形成於大革命時期的深港紅色通道,在華南敵後武裝游擊戰中,發揮了戰略物資運輸、愛國人士和國際友人的營救轉移、情報傳遞等重要作用,彰顯了深圳和香港兩地人民在民族存亡的危急關頭,團結一心、同舟共濟,攜手抗擊日本法西斯主義的偉大抗戰精神。
課題研究現狀
首先,從歷史背景而言。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以來,日本侵略者逐步蠶食中國領土,至1937年七七事變全面侵華戰爭爆發,中華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絕境。全體中國人民奮起反抗,打擊日本侵略者。深圳與香港因特殊的地理位置與戰略意義,成為抗戰的重要節點。深圳地處華南沿海,毗鄰香港,廣九鐵路貫穿其中,不僅是連接內地與外部世界的關鍵通道,也是敵後抗戰的重要戰場之一。香港作為國際港口城市,在抗戰時期扮演了中轉物資、傳遞情報及保護愛國人士的重要角色,其戰略地位尤為突出。然而,隨著日本侵略者對華南地區的軍事進攻與佔領,深圳與香港的政治與軍事環境急劇惡化。日本侵略軍在深圳實施殘酷的軍事佔領,嚴重破壞當地社會秩序與經濟基礎;日軍於1941年12月8日突襲並迅速佔領香港,開啟了長達三年零八個月的殖民統治,這一時期的殖民政策對香港社會產生了長久影響。因此,深入研究深圳與香港在抗戰中的特殊地位與作用,不僅有助於理解兩地在中國抗戰史中的貢獻,也有助於鞏固深港紅色紐帶、激活紅色記憶,為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提供歷史文化支持。
其次,從研究的必要性與深度廣度而言。學界對深港共同抗日的歷史已有初步研究,但對深港紅色通道及其歷史作用的研究關注不夠。一是現有研究多集中於宏觀層面的抗戰歷史敘述,而對紅色通道的具體運作細節缺乏深入探討。例如,關於紅色通道如何策劃、建立及運作的具體過程,目前尚缺乏系統的史料整理與分析。二是對於深港紅色記憶的傳承機制及其時代價值的研究相對薄弱。雖然部分文獻提及紅色記憶在當代社會中的重要性,但對其如何在家庭、社區及學校教育中得以傳承,以及在政治、文化、社會層面的價值,尚未形成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三是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與國際形勢的變化,必須鞏固世界反法西斯主義的價值體系,應當傳承深港共同抗日的紅色文化,弘揚時代價值。
再次,從研究目的而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教育引導全黨大力發揚紅色傳統、傳承紅色基因,賡續共產黨人精神血脈,始終保持革命者的大無畏奮鬥精神,鼓起邁進新征程、奮進新時代的精氣神。」本研究旨在全面還原深圳-香港紅色通道的歷史全貌,激活深港紅色記憶,挖掘深港紅色文化的時代價值。一是通過對歷史檔案、親歷者回憶及相關文獻的系統梳理,還原深圳-香港紅色通道的形成過程,揭示其在抗戰時期的關鍵作用與歷史意義。二是聚焦深港紅色記憶的形成與傳承機制,探討其在家庭、社區及學校教育中的傳播路徑與影響,分析其對當代社會的精神激勵與文化塑造功能。三是進一步挖掘深港紅色記憶的時代價值,從政治、文化、社會三個維度探討其對鞏固國家統一、傳承紅色文化及促進深港交流合作的現實意義。
第四,學術概念的釐定。本文採用了歷史記憶和文化價值理論。歷史記憶理論強調記憶的社會建構性,認為記憶並非單純的個體經驗再現,而是通過集體敘述、文化符號和儀式操演等方式被不斷塑造和傳承的過程。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論集體記憶》中指出,集體記憶是由社會群體共同創造和維持的,其目的在於強化群體認同和社會凝聚力。這一理論為理解深港紅色記憶的形成機制及其當代意義提供了重要視角。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認為,文化記憶是集體記憶的「制度化」和「神聖化」形態,具有更強的穩定性和傳承性。她提出記憶不僅是一種心理現象,更是一種文化實踐,通過物質載體(如紀念碑、文獻)和媒介形式(如文學、影視作品)得以延續和傳播。阿斯曼強調記憶的「文化性」和「制度性」,認為文化記憶不僅是過去的記錄,更是塑造群體身份認同和意義系統的核心機制。文化價值理論則從文化資本的角度闡釋了紅色記憶的傳承與時代價值。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認為,文化資本作為一種象徵性資源,能夠為社會群體提供身份認同和精神動力。
第五,從紅色文化再現與傳播角度而言。紅色文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創造的,蘊含著豐富紅色資源與厚重文化內涵的先進文化形態,是我們在前進道路上戰勝各種困難和挑戰、不斷奪取新勝利的強大精神力量。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深港抗戰歷史的研究逐漸增多,學者們主要聚焦於抗戰時期的具體歷史事件和人物,尤其是東江縱隊在香港大營救中的重要作用。孫瑞蓬在《打造紅色精品致敬百年征程——建黨百年主題廣播劇〈大營救〉創作談》中詳細描述了1941年底中國共產黨秘密營救困留在香港的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的偉大壯舉,展現了深港兩地在抗戰中的緊密聯繫。徐琳在《大時代背景下藝術群像刻劃的美學力量——〈明月幾時有〉評介》中通過對電影《明月幾時有》的分析,揭示了抗戰時期香港淪陷區的真實歷史背景以及東江縱隊等游擊隊的英勇事跡。這些研究通過文學、影視作品等形式,生動再現了抗戰時期深港地區的紅色記憶。研究表明,抗戰時期的香港不僅是國際物資中轉站,也是情報交流的重要樞紐,其戰略地位在東亞反法西斯戰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抗日戰爭時期的深圳與香港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有一段歷史是永遠都不能忘卻的,這就是從1931年到1945年歷時十四年艱苦卓絕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日軍因其凶殘和野蠻被稱為「獸軍」「日寇」,日本法西斯主義對人類文明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被永久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一)日寇入侵深圳與香港
1938年10月,日軍侵佔廣州後,逐步佔領包括深圳在內的珠三角部分地區。日寇採取了大規模轟炸、燒殺搶掠等手段,導致深圳地區(原寶安縣域)社會經濟和人民生命財產遭到嚴重破壞。深圳作為連接內地與香港的重要通道,使得日軍對其實施了嚴密控制,並試圖切斷抗日力量的物資供應和人員往來通道。在日寇鐵蹄下,深圳地區的農業生產停滯,商業活動被迫中斷,人民流離失所,社會陷入極度動蕩之中。日寇還通過建立偽政權和強化軍事管制,試圖鞏固在深圳的統治地位。日寇的野蠻侵略行動激起了當地人民的強烈反抗,點燃熊熊抗日烽火。
1941年12月8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同時,對香港發起軍事進攻,經過18天的激戰,英軍於12月25日投降,港督楊慕琦(Mark Aitchison Young)在投降書中簽字,香港自此進入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時期。由於英軍在聖誕節當天投降,這一天被稱為「黑色聖誕」,標誌著香港的淪陷。在此期間,日本侵略者對香港實施了極其殘暴的殖民統治和赤裸掠奪,如強制推行軍票、實行糧食配給制度,對華人社區進行歧視性管理。這些政策不僅摧毀了香港的經濟基礎,還導致社會秩序全面崩潰,民眾生活陷入極度困境。在這片黑暗之中,香港人民並未放棄抵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等抗日武裝力量在極端艱難的條件下展開了殊死鬥爭,為保護香港的文化精英和普通民眾作出了重要貢獻。
(二)深圳與香港的特殊戰略地位
深港因獨特的地理位置,在抗日戰爭中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深圳毗鄰香港,且廣九鐵路貫穿其中,使其成為連接內地與香港的重要樞紐。這一地理優勢不僅為抗戰時期的物資轉運提供了便利條件,也為人員往來和情報傳遞創造了關鍵通道。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深圳地區的黨組織充分利用這一地理條件,建立了多個抗日根據地和地下聯絡站點,為東江縱隊的活動提供了堅實保障。此外,深圳地區的險要地形和茂密叢林為游擊戰爭提供了天然屏障,使得抗日武裝能夠在日軍封鎖下靈活機動地開展鬥爭。深圳的戰略地位還體現在其對香港的支持作用上,兩地之間的密切合作構成了華南敵後抗戰的重要支撐點,為奪取華南抗戰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作為國際港口城市,香港在抗日戰爭時期扮演了多重重要角色。首先,香港是抗戰物資中轉的關鍵節點,大量來自海外的軍需品和醫療物資通過香港運往內地,為抗戰前線提供了重要支持。其次,香港在情報傳遞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複雜的社會結構和國際化背景為抗日情報網絡的建立提供了有利條件。此外,香港還是保護愛國人士和文化名人的重要基地。在日軍佔領香港後,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成功營救了大批文化精英和國際友人,將他們安全轉移至內地,這一行動被譽為「香港大營救」。這些事跡不僅體現了香港在抗戰中的特殊地位,也彰顯了其作為國際都市在民族危亡時刻的責任與擔當。正是由於香港在抗戰中的多重角色,其與深圳共同構成了華南敵後抗戰的核心區域,為抗擊日本法西斯主義作出了卓越貢獻。
深港紅色通道的形成和作用
(一)深港抗日紅色通道的形成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高度重視華南敵後抗日工作,並將其納入中共中央直接領導。深圳與香港成為中國共產黨開展敵後鬥爭的關鍵區域。據相關研究,深圳地區的黨組織在中共廣東省委的直接領導下,逐步建立起堅實的群眾基礎和抗日武裝力量,為紅色通道的形成提供了組織前提。與此同時,香港作為國際港口城市,不僅是物資中轉的重要樞紐,也是愛國人士和文化名人聚集地,其戰略意義不言而喻。然而,隨著日本侵略軍對華南地區發動全面進攻,尤其是1941年香港淪陷,深圳與香港之間的正常聯繫被切斷,建立一條秘密且高效的紅色通道成為當務之急。
從黨組織的發展情況來看,深圳與香港地區的黨組織在抗戰初期便已初具規模。深圳地區黨組織通過團結廣大人民,組織抗日武裝,逐步形成了以陽台山、惠寶邊坪山等根據地為核心的抗日力量網絡。而在香港,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則在淪陷期間秘密開展城市近郊和海上游擊戰,為紅色通道的建立提供了實踐經驗和軍事支持。
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高度重視和直接領導華南敵後抗戰工作,通過香港這一窗口與國際反法西斯力量保持聯繫,這使得深港紅色通道的建立不僅是地方性的需求,更是全國抗戰大局中的關鍵一環。
1937年10月的一天晚上,毛澤東把廖承志請到了他的窯洞,交給他一項重要任務,黨中央决定委派廖承志前往香港,開设香港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簡稱香港「八辦」)。1938年1月初,經先期抵港的廖承志、潘漢年、連貫等人周密籌建,香港「八辦」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號設立,對外稱粵華公司,以經營茶葉生意為掩護,搜集國際局勢信息,宣傳黨的抗戰主張,恢復整合香港等地中共組織,領導和發展抗日武裝力量,接收並轉運港澳同胞、海外僑胞及國際友人捐贈的抗戰物資。廖承志為辦事處主要負責人,潘漢年參與領導,連貫負責處理日常事務,李少石、張唯一、喬冠華、羅理實等20多位同志先後以各種合法身份和社會關係為掩護在辦事處工作。根據中共中央指示,香港「八辦」高度重視抗日武裝力量建設工作,積極領導、協助中共粵港地方組織建立和發展華南人民抗日武裝,先後建立東江抗日根據地、珠江抗日根據地、瓊崖抗日根據地等多個抗日根據地,這些抗日武裝成為香港淪陷後持久抗戰、保衛粵港人民的堅強力量,為粵港地區抗戰作出了傑出貢獻。1942 年 10 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香港「八辦」正式撤銷,人員轉入游擊隊伍繼續開展抗戰工作。
深港抗日紅色通道的建立是一個複雜而系統的過程,涉及多個關鍵時間節點和重要決策。根據歷史資料記載,紅色通道的策劃始於1941年底香港淪陷之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具體由香港「八辦」部署和實施),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迅速派出精幹武裝部隊進入香港,分三路直插新界地區,秘密開展抗日鬥爭。這些武裝力量在隊長黃冠芳、副隊長劉黑仔的帶領下,首先收集了英軍潰逃時丟棄的武器彈藥,建立了新界及九龍的抗日基地,設立了西貢墟地下聯絡機制,初步建立了深港抗日紅色通道。
1942年2月,陳達明帶著東江縱隊尹林平(政委)、曾生(司令員)的信到了港九,陳達明、蔡國樑和黃高陽在西貢開會。1942年2月3日,港九獨立大隊正式成立,大隊長蔡國樑、政委陳達明、政治處主任黃高陽,統一領導港九地區武裝鬥爭。這支隊伍後來發展到約1,000人,包括港九地區的工人、農民和熱血知識青年,下屬6個中隊。有長槍隊、短槍隊、海上武裝隊、城區地下武裝隊和情報系統等。東江縱隊在深圳地區建立了多個抗日根據地,並通過廣九線貫穿其中的地理優勢,逐步打通了連接深圳與香港的物資運輸線路。在此過程中,黨組織還制定了詳細的行動計劃,包括利用海上航線進行物資運輸,以及通過陸路交通線轉移人員,確保通道的安全性和高效性。紅色通道的建立得到了當地群眾的廣泛支持,許多村民和漁民積極參與到物資運送和情報傳遞工作中,為通道的順利運行提供了重要保障。
至1943年,隨著東江縱隊力量的不斷擴大,深港抗日紅色通道的作用不斷發揮,不僅承擔了物資運輸的任務,還成功實施了多次營救行動,如著名的「香港大營救」,將數百位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安全轉移至內地。這一系列舉措標誌著紅色通道從初步建立到全面運作的轉變,同時也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在極端困難條件下卓越的組織能力和戰略智慧。
(二)紅色通道的參與人員及其分工
深圳—香港紅色通道的運作離不開黨組織領導人員的精心策劃與堅強領導。其中,東江縱隊相關領導人起到核心作用。曾生作為東江縱隊的司令員,不僅直接參與了紅色通道的規劃與實施,還在抗戰中展現了非凡的決策智慧與領導才能。他在抗日戰爭爆發後,積極組織香港海員進行離船罷工等形式的抗日鬥爭,為紅色通道的建立積累了寶貴經驗。此外,黃冠芳和劉黑仔作為港九獨立大隊的隊長和副隊長,在紅色通道的具體運作中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率領游擊隊深入新界及九龍地區,建立了多個抗日基地,並成功開闢了西貢墟地下聯絡機制,為通道的安全運行提供了堅實保障。
這些黨組織領導人員不僅在戰略層面制定了詳細的行動計劃,還在實際操作中展現了高度的靈活性與創新性。例如,在面對日軍嚴密封鎖的情況下,他們充分利用深圳與香港之間的地理優勢,設計出了多套備用方案,以確保物資和人員能夠順利通行。同時,他們還注重發動群眾力量,通過廣泛動員當地村民和漁民參與通道運作,極大地提升了通道的隱蔽性和可持續性。正是由於這些領導人員的卓越貢獻,深港紅色通道才能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下始終保持高效運轉。
在深港紅色通道的運作中,游擊戰士的英勇事跡與無私奉獻成為紅色記憶的底色。交通員、游擊隊員以及其他普通民眾構成了紅色通道運行的中堅力量。例如,許多交通員冒著生命危險穿梭於深圳與香港之間,負責傳遞情報和引導人員轉移,其工作的高效性與隱蔽性直接關係到通道的安全運行。而游擊隊員則承擔了保護物資運輸線路、打擊日軍巡邏隊等重要職責,在戰鬥中展現出頑強的意志和不怕犧牲的精神。
香港當地的村民和漁民積極參與到紅色通道的運作中,為物資運送和人員轉移提供了重要支持,充分展示了深港兩地人民為抗擊日本法西斯主義而團結協作、英勇戰鬥的不屈精神。
(三)紅色通道的物資與人員運送
深港紅色通道在抗戰期間承擔了重要的物資運輸任務,其運送方式多樣且靈活,充分體現了黨組織在極端困難條件下的智慧與創造力。根據歷史資料記載,紅色通道主要通過海上和陸路兩種途徑進行物資運輸,以應對日軍對交通線的嚴密封鎖。
在海上運輸方面,黨組織充分利用了深圳與香港之間便利的海上航線,派遣熟悉海況的漁民駕駛小船往返於兩地之間,運送包括武器彈藥、醫藥用品和糧食在內的各類抗戰物資。這種方式雖然風險較高,但由於船只體積小、行動隱蔽,往往能夠成功避開日軍的巡邏與搜查。
在陸路運輸方面,紅色通道則依託深圳地區的抗日根據地,通過廣九線貫穿其中的地理優勢,開闢了多條秘密交通線。這些交通線通常由游擊隊員負責保護,沿途設有多個隱蔽的中轉站,用於存放和轉運物資。為了確保物資運輸的安全性,黨組織還制定了嚴格的保密措施,例如使用暗號識別身份、避開日軍據點等,從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物資被截獲的風險。
此外,當地群眾也積極參與到物資運輸工作中,利用老百姓身份或夜間行動等方式,協助完成了大量物資的轉運任務。正是通過這些靈活多樣的運送方式,紅色通道得以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持續保障抗戰物資的供應,為抗戰勝利提供了重要支持。
深港紅色通道不僅承擔了物資運輸的任務,還在保護愛國人士、營救文化名人和國際友人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香港大營救」發生在1941年底香港淪陷之後。按照周恩來的指示,香港「八辦」協同華南地區黨組織,秘密將800多位被困在香港的愛國民主人士、文化名人以及國際友人安全轉移至內地。這些人員包括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茅盾、夏衍、沙千里、胡繩、梁漱溟等300多人,還包括被近百名日軍關押在集中營的英軍官兵和英國、印度、荷蘭、比利時等國僑民,以及國民黨駐港代表海軍少將陳策,國民黨高級官員余漢謀、吳鐵城等人的多位家屬。大營救極大增強了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與信心,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在轉移過程中,紅色通道採取了多項措施以確保人員的安全性和隱蔽性。例如,黨組織利用西貢墟地下聯絡機制,安排專人接應,並引導被營救人員通過海上航線撤離香港,再經由深圳地區的抗日根據地如白石龍、陽台上、大鵬、葵涌等地轉移至內地。同時,為了避開日軍的搜查,轉移行動通常在夜間進行,並借助當地群眾提供的掩護,利用民宅作為臨時藏身之處。此外,游擊隊員還負責沿途的安全保衛工作,多次成功擊退了日軍的巡邏隊。
紅色通道在營救國際友人方面也展現了高度的人道主義精神。例如,一些外國記者和救援人員通過紅色通道得以安全撤離香港,並將抗戰真相傳播至國際社會。這些事跡不僅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寬廣胸懷,也為深港紅色記憶的形成增添了獨特的內涵。
深港紅色記憶的形成與傳承
(一)紅色記憶的核心內容:抗戰中的英勇事跡
抗日戰爭期間,深圳與香港地區的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展開了艱苦卓絕的鬥爭,湧現出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作為香港抗戰期間唯一一支成建制的抗日武裝力量,深入新界及九龍地區,收集英軍潰逃時遺棄的武器裝備,並迅速建立起抗日基地和地下聯絡機制。游擊隊員們開創性地開展城市近郊和海上游擊戰,為我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斬竹灣村的烈士碑園記錄了游擊隊員們在極端困難條件下浴血奮戰的歷程,其碑體模仿步槍外形,象徵抗日武裝力量的不屈意志。此外,深港兩地的民眾也積極參與到支援前線的工作中,他們為游擊隊提供物資、情報,甚至直接參與戰鬥,展現出團結協作、不怕犧牲的精神,深深烙印在深港人民的心中,成為紅色記憶的核心內容。
深港地區的紅色記憶還體現在普通民眾對抗日英雄的緬懷與紀念上。例如,新界西貢區及烏蛟騰村的兩座抗日英烈紀念碑,靜靜佇立於群山環抱之中,深埋著港九大隊出生入死的歷史記憶。這些紀念碑不僅是歷史的見證,更是後人銘記先烈英勇事跡的重要載體。通過親歷者回憶和歷史文獻的整理,可以清晰地看到深港人民在抗戰中的無私奉獻與堅定信念。正是這些英勇事跡的代代相傳,使得深港紅色記憶得以不斷豐富和深化。
特殊歷史事件在深港紅色記憶的形成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香港大營救」事件。這一壯舉不僅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國家危難時刻的中流砥柱作用,也彰顯了深港人民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的深厚情感。
首先,凸顯了中國共產黨在極端困難條件下保護文化精英的決心與智慧,增強了深港人民對黨的信任與認同。其次,營救過程中涉及的複雜路線與周密部署,進一步展現了深港紅色通道的重要性。最後,在深港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集體記憶,成為紅色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記憶不僅強化了兩地人民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知,也為後世傳承紅色文化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二)深港紅色記憶的傳承
深港紅色記憶的傳承主要體現在家庭與社區的日常講述以及學校教育與文化傳播的系統性推廣中。家庭傳承與社區傳承相輔相成,共同推動了紅色記憶在深港地區的延續與發展。
在深圳與香港的許多家庭中,老一輩人常常通過講述抗戰時期的親身經歷或耳聞目睹的故事,向晚輩傳遞紅色記憶。這種面對面的交流不僅使年輕一代能夠更直觀地了解抗戰歷史,也讓他們感受到先輩們的無私奉獻與愛國情懷。
社區活動則是紅色記憶傳承的另一重要形式。在深圳與香港的部分社區,每年都會舉辦紀念抗戰勝利的主題活動,如祭掃烈士陵園、重走抗戰路線等,生動再現抗戰時期的歷史場景。此外,社區還邀請抗戰親歷者或專家學者舉辦講座,進一步深化居民對紅色記憶的理解。這種家庭與社區相結合的傳承方式,不僅增強了深港人民對紅色記憶的認同感,也為後代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實踐平台。
學校教育與文化傳播在深港紅色記憶的傳承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學校層面,深圳與香港的中小學普遍通過課程設置與文化活動,將紅色記憶融入學生日常學習中。深圳市羅湖區推出「行走的思政課」項目,通過組織學生實地考察紅色遺址、參與情景模擬等方式,讓學生在親身體驗中感受抗戰歷史。這種沉浸式教學方法不僅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也幫助他們更好地理解紅色記憶的時代價值。
文化機構則在傳播紅色記憶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深圳與香港的博物館、紀念館等文化場所通過舉辦專題展覽、出版相關書籍等形式,廣泛宣傳抗戰歷史與紅色文化。例如,深圳的黨史館和香港的歷史博物館均設有專門的抗戰展區,通過實物、圖片和多媒體展示,生動再現深港地區在抗戰中的英勇事跡。多元化的傳播方式不僅擴大了紅色記憶的影響力,也為深港兩地的文化交流與合作提供了契機。
深港紅色記憶的時代價值
(一)政治價值: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深港紅色記憶作為中華民族團結一心、共同抵禦外敵精神的重要體現,對鞏固國家統一和增強民族凝聚力具有深遠意義。在抗日戰爭時期,深圳與香港地區的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展現出高度的合作意識與愛國情懷,這種精神不僅成為抗戰勝利的重要支撐,也為當代國家統一提供了歷史借鑒。偉大團結精神的內生邏輯表明,中華民族在歷史長河中形成的向心力、行動力和意志力,是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核心動力。通過深港紅色記憶的傳承,可以進一步激發民眾對國家統一的認同感,尤其是在當前複雜的國際形勢下,這種精神力量更顯珍貴。
深港紅色記憶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生動素材,對培養公民愛國情感和樹立正確的國家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深圳紅色文化資源融入黨史學習教育的研究表明,紅色記憶能夠有效增強青年學生和黨員同志的理想信念,明晰奮鬥方向。深港紅色記憶不僅是歷史的見證,更是強化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工具,有助於塑造新時代公民的國家意識和責任感。
(二)文化價值: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融合
深港紅色記憶是紅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傳承紅色基因、弘揚革命文化具有獨特作用。紅色記憶作為中國共產黨革命歷史文化的記憶建構,在當代語境中承載著鮮明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其通過記憶喚醒、建構和刻錄實現了表達、維護和認同的功能。紅色文化不僅是粵港澳大灣區同根同源的重要見證,更是推動教育合作和建設人文灣區的寶貴資源。深港紅色記憶以其豐富的歷史內涵和鮮明的地域特色,為大灣區紅色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特別是在提升港澳青年國家認同方面具有現實意義。
與此同時,深港紅色記憶還豐富了深圳與香港的地域文化內涵,為兩地文化發展增添了獨特魅力。深圳作為改革開放後崛起的新興城市,其紅色文化資源蘊含著豐富的史學價值和時代價值;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其紅色記憶則體現了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的獨特歷史風貌。通過挖掘和傳播深港紅色記憶,不僅可以促進兩地文化的交流與融合,還能為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建設注入新的活力,從而推動區域文化的多元化發展。
(三)社會價值:促進深港社會互信和攜手進步
深港紅色記憶作為兩地共同的歷史記憶,對增進人民相互了解、促進交流合作具有重要價值。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的抗戰事跡表明,深港兩地在抗擊日本法西斯主義的過程中形成了深厚的血肉聯繫,這種聯繫不僅體現在戰鬥中的相互支持,也反映在戰後兩地在經濟、文化等領域的深度合作。因此,深港紅色記憶不僅是歷史的回顧,更是推動當前深港交流合作的重要紐帶,有助於增進兩地人民的感情與信任。
深港紅色記憶所蘊含的精神對營造和諧社會氛圍、激勵人們奮發向上具有積極作用。紅色記憶中的英勇事跡和無私奉獻精神,能夠激發社會成員的集體榮譽感和使命感,從而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例如,深圳地區黨組織在抗戰中建立的陽台山、惠寶邊坪山等抗日根據地,不僅為抗戰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也為當地群眾樹立了團結協作的榜樣。在當代社會,這種精神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能夠激勵人們在面對困難和挑戰時保持堅韌不拔的意志,共同推動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深港抗日紅色通道的形成、發展和作用,彰顯了深港人民共同抗擊法西斯主義的英勇事跡、英雄人物和歷史貢獻,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團結率領全中國人民,共禦外敵、保衛家園的抗戰精神和中流砥柱作用,揭示了深港紅色通道在物資運輸、人員轉移及情報傳遞等方面的關鍵作用。總之,激活深港紅色記憶,弘揚深港紅色文化,重走深港紅色通道,對促進「一國兩制」事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深港融合發展都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和實踐價值。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5年7-9月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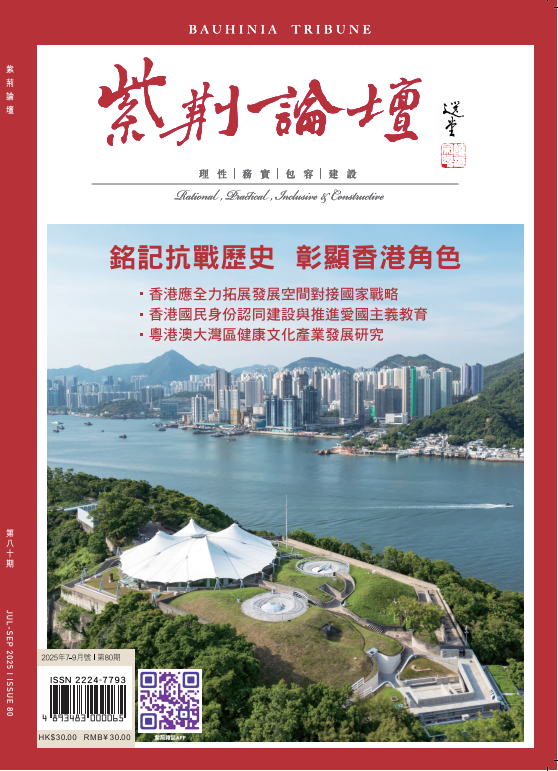







 今日熱搜
今日熱搜

 本週熱搜
本週熱搜

 本月熱搜
本月熱搜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