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26日,《學習俱樂部》首發了著名經濟學家、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先生關於《十五五:三“重”命題的趨勢、短板與建議》(發言錄音及PPT),引起讀者關注並留言:“希望看到錄音文字稿”。現由常教授本人根據錄音及PPT整理加工成此文,相對於會上因受時間限制的簡短發言而言,本文字稿更完整也更有學術價值,現刊發,以饗讀者。
我發言的題目是《十五五:三“重”命題的趨勢、短板與建議》。三“重”命題,十五個字——“創新重數智、發展重人本、改革重要素”。圍繞每個命題,各作三層分析:趨勢、短板及建議,與大家交流、探討。
一、創新重數智
我用“數智”二字:意指數字技術革命是基礎,人工智能是其新的發展階段,或曰“提升”。
(一)趨勢(應然分析)
這裡說的創新主要指“科技創新”,總的趨勢是什麼?我在主筆出版的《創新立國戰略》(列入國家發展戰略叢書,2013,學習出版社等聯合出版)一書指出,從戰略層面看,國家應走“創新立國戰略”之路,以切實推動我國從“加工大國”向“創新大國”跨越。從科技創新本身而言,數字革命與人工智能(AI)是核心趨勢。
去年(2024)我曾四次到杭州考察、學習,當地的“六小龍”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它們不僅在技術上開源、免費、低成本(這有利於推進“平權化”、擺脫貴族化),更在生產關係上呈現鮮明特點:第一,全都是民營企業(不是國有企業);第二,全都由年輕人領軍。這讓我思考,在中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後,“人才紅利”特別是年輕人的“人才紅利”已開始萌生,我國或許正進入“人才紅利”發展的新階段。
今年初,浙江開“兩會”,他們訪談,我在1月13日《浙江日報》提出“創新三建議”,其中,第一條就是建議浙江全省推廣DeepSeek(“深度求索”)模式;半個月後,1月29日(中國春節期間),DeepSeek在海外爆火,引起關注。
當然,我知道,DeepSeek還不是原始創新,而屬於一種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AI就本身來說,現在也尚處於“一般”人工智能階段,下一步應向通用人工智能(AGI)及更高階段的超級人工智能(ASI)發展。這也引發我的思考:下一步我們人類將面臨怎樣的變革,未來將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呢?
(二)短板(實然分析)
我國在高科技領域面臨嚴重的“卡脖子”問題。中美之間,從五月瑞士日內瓦會談——到六月英國倫敦會談——再到七月瑞典斯德哥爾摩會談,雙方博弈顯示,在高科技領域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存在相互“卡脖子”問題。雖然我們手中也有“殺手鐗”——“稀土”(包括佔全球61%的稀土資源和佔全球90%以上的稀土精煉產能、技術與產品),但在高科技(例如芯片等)關鍵領域,我們確實也有“短板”。
這意味着,中國必須“強化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這是“十五五”我國必須突破的“瓶頸”。
(三)具體建議(四條):
一是強化創新精神。我認為,“自立自強”不僅是科技領域“單向度”的自立自強,而應是整個國家“民族性”的“自立自強”,此乃“國之魂”。欲實現科技自立自強,必須培育和鑄就整個民族的自立自強精神。
在這一點上,要學浙江“古越人”那種“臥薪嚐膽”的精神(《勾踐棲會稽》載:夜間每過一更天,衛士就喊一句:“勾踐,你忘了會稽之恥了嗎?”“沒有忘記”)。當代中國,亟需這種全國上下“自強不息”的精神。
二是營造創新環境。圍繞創新者“心靈放飛”,首先要構建類似“大森林”般的大環境,同時也要培育“小樹蔭”式的小環境,即使一時難以形成“大森林”,也必須給創新者提供一個“遮陰蔽日”的“小樹蔭”,好讓他們“心靈放飛”。如果大家“心靈不放飛”,你就是空談創新。
三是完善創新機制。既要有宏觀調節機制,也要有微觀的“產權”機制。這裡的關鍵是科創人員“職務發明”成果的產權分割機制。筆者在拙著《廣義產權論》(中國經濟出版社,2009)曾提出:“還應將這部分‘知識’產權的一部分,分配給具體創造該‘知識’產權的技術人員。”即:“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該單位所有,另一部分由技術人員持有”(見該書,第207頁)。
但,這些年,現實中教訓慘痛,一些創新者因產權分割受到不公正對待(甚至被抓),這種“悲劇”無論如何不能再重演(已發生的,也要甄別、糾偏)。必須落實科創人員的“產權”,而且不應使用“恩賜式”的“賦予”提法,建議用“尊重和承認”或類似提法為好。當然,現在我們可不去計較“提法”問題,“賦予”終究比不“賦予”好。
四是推動國家層面編制並公布“中國創新指數”。目前“全球創新指數”由聯合國知識產權組織與美國康奈爾等大學聯合編制(中國的排名大體可以)。國內呢,我們現在也有研究部門(如科技部科技戰略研究院)編制。我建議,十五五進一步提升層次,即提到國家層面,編制並公布中國的“國家創新指數”。
(四)由科技創新引發的個人進一步思考:
今天有很多老朋友在座(也有些新朋友),我們坦誠討論一個涉及現代化問題:
日本明治維新前,教育家福澤諭吉講過一段話:“一個民族要崛起,須改變三方面:人心(思想)、制度、器物”。這三者現代化,理論上是否有邏輯呢?實踐上是否有順序呢?我認為,理論上應該是有邏輯的,實踐操作起來也應是有順序的。
當前,我們國家層面高度重視“發展新質生產力”,很好。我認為,新質生產力本身也包括了思想和制度的元素,但是,人工智能AI這等技術本身可能還屬於器物的現代化,應屬於第三個現代化吧?面對今天這個格局,我們能不能從實際出發,可否提高一層,抓住“新質生產力”作為一個切入點,作為一個突破口,向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某些環節推進。
具體建議:當前應深入研究人工智能AI對制度(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影響或者“倒逼”問題。《浙江日報》5月26日“思想周刊”刊登了我的論文《十五五時期經濟發展與改革思路初探》,提出了“三層倒逼論”,即以發展新質生產力為突破口、為切入點,實行“三層倒逼”:第一層倒逼“生產方式”(介乎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如經濟結構問題),第二層倒逼生產關係(即經濟制度、經濟體制問題),第三層倒逼上層建築的“某些環節”(我這裡只說是“某些環節”問題,並非上層建築之全部)。
二、發展重人本
(一)人類發展大趨勢
當年,在南開大學經濟系讀政治經濟學進修班時,老師教“社會主義經濟經典著作選讀”,第一本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2月出版的《共產黨宣言》。書中講的一句話記憶深刻:“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學後感到,這是《共產黨宣言》中最閃光的思想。
現在簡化成“人的發展”,其實,馬克思原話是“每個人”和“自由發展”。我理解,“人”是抽象的,“每個人”具體的;發展是可貴的,自由發展是價更高的(“發展誠可貴,自由發展價更高”)。因此,這兩個前綴詞是不可刪節的。2018年紀念《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周年,出了最新版,我看了2018年新版,依然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我認為應尊重《共產黨宣言》的這個原意。因為,馬恩提出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這一理念不僅揭示了“發展的本質”,更揭示了“新社會的本質”。
當代國際上有良知的經濟學家也秉持這一發展理念。例如,本人在《人本體制論》一書(中國經濟出版社,2008)中,曾引述了法國經濟學家佩魯(Perroux)的“人本主義發展觀”。他在其代表作《新發展觀:基本原則》(1983)中指出:“真正的發展,必須是經濟、社會、人、自然之間的全面協調共進”,核心是“人”。
阿馬蒂亞·森(Sen.Amartya)憑什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是他的《以自由看待發展》,書中強調發展的本質在於“擴展人的可行能力”。
我認為,這些是“人類的共同文明”。最近(2025年7月10日至11日),北京不是正在召開“全球文明對話”部長級會議嗎”?(中宣部和中聯部主辦)。既然要“樹立平等互鑑對話包容的文明觀”,我們得把“人類的共同文明”旗幟高高舉起來才對。
正是在共同理念的基礎上,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於1990年5月首次公布人類發展指數(HDI),將單一GDP指標轉變為“綜合性評價指標”,作為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本人曾研究過這個“指數”,認為它反映了人類的共同價值和發展的大趨勢。
(二)短板分析
我國的“人類發展指數”情況如何?首先應該承認,2012年(十八大)以來的十幾年,是有進步的。有數據為證:2012年排在世界第101位,2017年上升至第86位,到今年(2025公布)升至第78 位。但是,我國的GDP在全世界排第二位的。很明顯,人類發展指數第78 位與GDP全球第二的排名,存在着較大的落差。
而更應引人憂慮的是,在浮躁的社會氛圍中,有些媒體盲目地渲染“厲害了我的國”云云,以至於,全社會講GDP“全球老二”者,眾;講HDI“全球第78位”者,寡。
對此,我自己很憂慮:對第二位與78位之間這個落差,怎麼辦啊?“人類發展指數”是要落到“每個人”的“人頭”上的,同志們。按照黨中央一再強調的“實事求是”精神,這種社會浮躁心理必須改變,我們有很大的探索空間和改革空間。
(三)建議:
由此,我建議將人類發展指數納入“十五五”相關指標。該指數包含三大核心內容,第一個是人的生命健康,特別是長壽,這個指標非常好;第二個是知識的獲取,包括教育年限和教育水平。這個對我們來說太關鍵了;第三是生活水平,包含人均GDP等,它能更全面反映人的生活質量。因此,“十五五”我們是不是抓住“人類發展指數”來落實“發展重人本”?
與此相聯,我順便提一下與民生直接關的“居民消費”問題。現在,研究中國的消費,涉及“消費六率”。包括:“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消費增長率”、“消費貢獻率”、“最終消費率(含政府消費)”、“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傾向”。“消費六個率”各有各的內涵,也各有各的用處,都不應否定。
現在,電視報紙等媒體宣傳、更加廣為人知的是“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這一指標確實反映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現實增長情況(大家也都比較習慣),但是根據自己的研究,這一指標存在兩個重要缺陷:
其一,按照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指標內涵,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主要包括商品性消費+“餐飲類服務性消費”,它除了不包括“非實物商品”的網上零售額外,更重要的是,它不包括除餐飲服務外的其他大量的“服務性消費”(如住宿居住、交通通訊、教育培訓、醫療健康、旅遊體驗、文化娛樂,以及其他用品服務等多領域的服務消費支出)。
而根據最新數據,中國居民“人均服務性消費支出”已經佔到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46.1%(即央視說的“老百姓每花10塊錢,4.6元‘買服務’而不是‘買實物”)。可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雖然包括部分交叉性的“餐飲消費”,但不包括絕大部分的服務性消費。而居民“服務性消費”,正是我國在當前和下一步要大力激發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已經不能適應居民“服務性消費”增長的新格局。
其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既“短缺一大塊”,又“多出一大塊”,即:相對於居民而言,多出了“機關、社會團體、部隊、企事業單位等”)的消費支出。根據相關數據及分析,從支出法核算GDP角度研究,最終消費由居民消費和政府等消費這兩部分構成,兩者相加中國現在為54%,其中:“政府消費率”長期在15%左右(即政府消費在最終消費中佔到30%),“政府消費率”( 15%)是不應該算在居民消費頭上的。現行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多出了政府消費這塊,是應該“剔出”的(其他不再分析,略)。
比較起來,從戰略上說,我建議國家應更加重視和側重抓“居民消費率”。
“居民消費率”是“居民最終消費支出”與“支出法GDP”之比,近年來,中國居民消費率具體數據如下:2022年居民消費率為37.2%(低於38個可比國家53.8%的平均水平);2023年中國居民消費支出(公式之分子)493,247.2億元,GDP(公式之分母)為1,262,642.5億元,居民消費率為39.2%。這39.2%處於什麼水平?這裡不便引用國際比較相關的數據,簡言之,國際比較,很低(不僅低於發達國家,而且低於一些發展中國家)。
我認為,居民消費率是研究消費的“十環”之所在(當然箇中比較複雜,難度也大),應作為國家監測和考核指標。第一,有利於真正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促進“每個人”的發展;第二,也有利於提高中國全民族凝聚力,應對國內外風險挑戰;第三,更有利於提高我在國際社會中的排名位次,強化我國在國際競爭中的戰略主動權。
至於老百姓關注的“支出法GDP,都支出到哪裡去了”?這是另一個更宏觀的命題,很值得研究,以回答老百姓的“時代之問”(擬另文論述,本文不再展開)。
三、改革重要素
(一)趨勢
十五五期間,中國改革將出現什麼新趨勢?就經濟領域而言應該抓什麼?我認為,應該抓“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這是改革的新趨勢。
2024年12月,由本人主筆、蔡繼明教授副主筆,並帶幾位年輕朋友耗費四年心血完成的新著《中國要素市場化配置大綱》(54萬字),已由廣東經濟出版社出版,並被中宣部列為“2024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基於新趨勢的需要,我們重點聚焦於七大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功能與收入分配功能”,這是十五五必須面對的問題。
(二)短板
中國改革已過46年,前一階段的“商品市場化改革”之戰,打得很艱苦,也取得不小成效,2021年,中國商品和服務價格的市場化程度已達到97.5%。但是,相比之下,七大要素的市場化配置改革長期滯後,成為中國改革的短板。
例如,土地、技術的市場化程度較低;數據要素的產權問題,有的已破題,有的尚未完全破題,如“人臉識別”數據的產權界定和產權交易等;至於“管理要素”(企業家要素),雖然中央已經列入“七要素”之中,但是我們的文件、報告、講話等,對此仍然採取迴避態度,以至於至今“管理要素”(企業家市場)處於“缺位”狀態,這是“不可或缺”的。基於此,我在書中專門寫了第十章:強調“不可或缺的”管理要素(企業家市場)。總之,這些“短板”必須補上。
(三)建議
為提高中國的全要素市場化指數,建議十五五期間,可從“市場配置功能與收入分配功能”相統一的更高層次,“雙線”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
雙線”之一:發揮要素市場化改革的市場配置功能。去年我在全國縣域經濟發展大會上提出“要素三放論”,即:“人本要素要放手”;“物本要素要放活”;“數據要素要放量”,十五五期間應秉持“要素三放論”。
雙線”之二:發揮要素市場化改革的收入分配功能。黨中央在國內學者多年研究(包括南開學者谷書堂教授和蔡繼明博士1988年首次提出“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理論”)基礎上,借鑑當代人類共同文明的成果,確立了“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思想:
從中共十六大(2002)提出這一“原則“,到中共十七大(2007)提出這一“制度”,再從中共十八大(2012)提出:“完善”這一“初次分配機制”,再到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2013):提出“健全”這一“報酬機制”;再到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2015):提出“優化”這一“機制”……
特別是,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2019):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包括“七要素”在內的“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直到去年(2024年)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一字不易地賡續十九屆四中全會上述關於“……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
正是在學界此前多年探討基礎上,深入學習和領悟中央自十六大以來一系列文件的一貫思想,本人經進一步思考研究,於今年(2025年)1月9日在《中國經濟導報》訪談中,提出要素分配功能的“唯一標準論”——即“要素貢獻是決定要素報酬的唯一標準”“市場是評價貢獻的基本尺度”。1月10日《中國改革報》轉載(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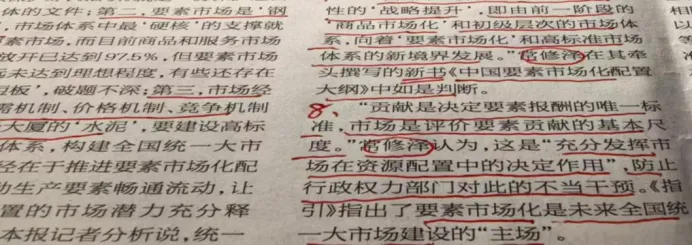
這裡,我嘗試提出“唯一標準論”,“唯一”就不是“唯二”。我希望:不要離開中央上述《決定》提出的這個“標準”,再去另立“別的”標準。
以上觀點,願與學界朋友共同切磋。







 今日熱搜
今日熱搜

 本週熱搜
本週熱搜

 本月熱搜
本月熱搜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